譯者:林巧玲、許宏彬
出版品牌:左岸文化
出版日期:2016-12-21
產品編號:978986572738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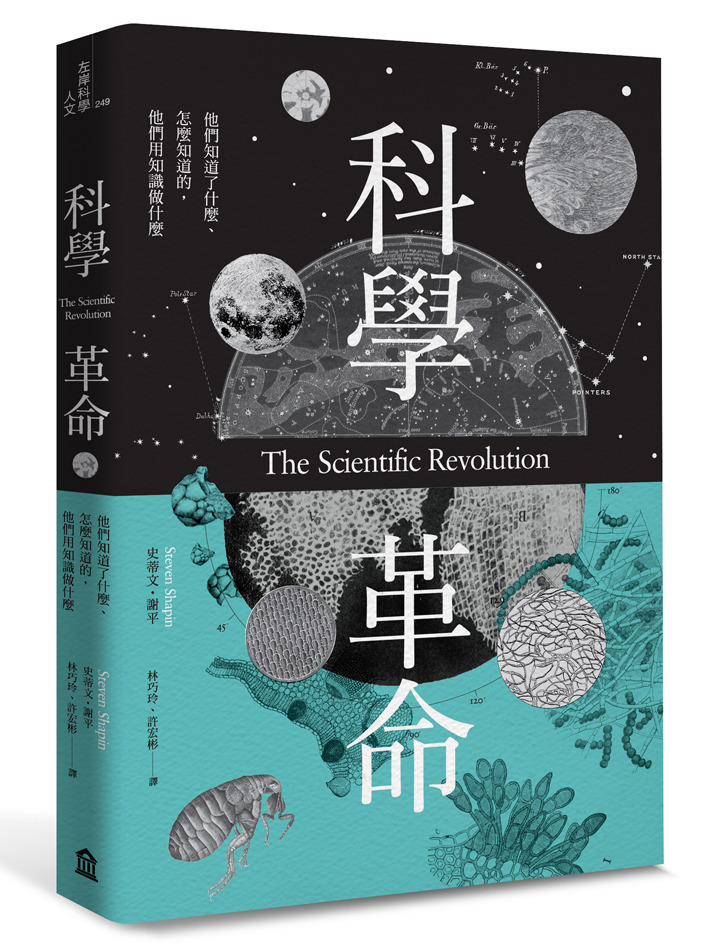



科學從來就不是中立的,也並非一項純粹追求真理的事業;不過它仍是人類關於自然世界最可靠的知識。
1939年,法國哲學與歷史學家夸黑提出「科學革命」一詞,並盛讚其為自希臘時代以來,「人類心靈所達到,或說所遭逢過最深遠的革命。」幾年後,英國歷史學家巴特菲爾德說,科學革命的「光芒掩蓋了基督教崛起之後的一切成就,它讓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顯得只不過是歷史的插曲……(科學革命是)現代世界與現代心智狀態的真正起源。」
「科學革命」的概念我們都很熟悉,不過究竟什麼才是科學?什麼才是科學史討論的對象?十七世紀種種「新」觀點、「新」方法,真的與之前的歷史無關?歷史究竟是連續、還是斷裂的?本書作者謝平開宗明義,介紹十七世紀西歐重要的科學成就,再發揮其科學知識社會學的專長,分析並探討「科學事實」如何在複雜的社會過程中取得正當性,以及如何從科學、宗教以及國家力量的複雜關係,來理解十七世紀追求科學知識的動機與條件。
本書從啟蒙時代講起,第一章處理了一般談論科學革命時會提及的標準議題,包括當時對亞里斯多德自然哲學的挑戰、以哥白尼的太陽中心論取代地球中心論,以及利用機械比喻自然的說法。第二章把討論焦點轉向那個時代的人是如何更積極、更務實地「製造」知識這回事。第三章將自然知識所服務的一系列目的,置於十七世紀具體的歷史時空之中。自然知識並不只是信念,某個程度它也是資源。
謝平將科學革命置於社會脈絡中解讀,累積十餘年有關「科學革命」的歷史研究,集合各家說法,呈現對「科學革命」的最新詮釋。
史蒂文.謝平(Steven Shapin, 1943-)
謝平是位具有歷史意識的社會學者,也是位具有社會學意識的歷史學者,被視為1980年代興起之「科學知識社會學」(the 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SSK)的重要旗手之一。他曾任職於愛丁堡大學科學研究小組、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社會系,現為哈佛大學科學史系福特講座教授。謝平曾於2001年獲科學之社會研究學會頒發貝爾納獎(John Desmond Bernal Prize),該獎項意在表揚長期致力探討科技的社會層面之傑出學者。
謝平著有多部討論科學知識社會史的作品。《真理的社會史》(A Social History of Truth: Civility and Science in Seventeenth-Century England)曾於1996年獲頒科學之社會研究學會的弗萊克獎(Ludwik Fleck Prize),以及美國社會學會的莫頓獎(Robert K. Merton Prize)。與賽門.夏佛合著的《利維坦與空氣泵浦:霍布斯、波以耳與實驗生活》(2006年,行人出版)獲2005年伊拉斯莫斯獎(ErasmusPrize);荷蘭國王(當時尚為王儲)威廉-亞歷山大在頒獎時讚譽兩位教授「全然改變了我們對科學與社會的看法」。
林巧玲
清華大學歷史所科技與社會組碩士。目前任職於出版社。
許宏彬
中興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研究興趣為醫療史、身體史與科技與社會(STS)研究。
導論(摘錄)
為什麼還要書寫科學革命?
還有其他理由使得歷史學家對於科學革命的既有範疇感到不安。首先,近年來,歷史學家不再認為單一的思想觀念可以在概念空間裡自由地流動。過去,學者把「科學革命」視為獨立的概念或抽象的心理狀態,但新的解釋則堅持,觀念是更廣泛的文化與社會脈絡的一部分。如今我們對十七世紀科學變遷和宗教、政治以及經濟模式之間的關係有更深刻的理解。其次,更根本的是,一些歷史學家希望以具體的人類實作為研究對象,因為概念或觀念是從具體的人類活動中誕生的。我們應該關心,當人們進行或確認一個觀察、證明了一條公式,或完成一項實驗時,實際上做了什麼?將科學革命理解成「人類的活動史」,會非常不同於把它理解成(自由流動的)概念的「概念史」。最後,歷史學家對「誰」創造了科學革命,也很感興趣。什麼樣的人開創了這樣的變革?當他們點燃這場革命之火,同時代的人都相信他們嗎?還是只有一小部分的人相信?如果只有非常少數的人參與,我們為什麼會說科學革命是個影響「我們」重新看待世界的重大革命?為什麼會說科學革命開啟了「我們」此刻的現代性?這一連串的問題若不解決,將變成我們在使用科學革命這個概念時,習焉不察的陷阱。要回答這樣的問題,意味著我們得對現代早期的科學變革有套解釋,以符合我們這個凡事較不斬釘截鐵,但充滿好奇心的時代。
即便有這些合理的懷疑與不確定,書寫科學革命仍是有意義的。主要的考量有兩個,第一,許多十六世紀晚期和十七世紀的重要人物都曾明確表示,他們致力推動非常新穎、重要的自然知識,並發展新的實作,人們透過實作,獲取、評價和交流正統的知識。他們認為自己是「現代論者」,有別於「傳統」的思考與實作模式。在這層意義上,今日所謂「科學革命的巨變」來自他們(和被他們攻擊的人士)的說法,科學革命來自二十世紀中葉的歷史學家發明一說,實則過於簡化。所以我們可以這麼說,十七世紀有人有意識且大規模地改變人們對自然的信念,以及獲取自然知識的方法。一本探討科學革命的書理應告訴讀者當時的這些企圖,不論這些企圖當時是否成功,以及彼此之間是否相互競爭、或是矛盾。
但是為什麼我們選擇只說某些故事,而不說其他的呢?如果在十七世紀,不同的人持有不同的世界觀,我們該如何挑選我們的主角和他們的信念?例如,某些「自然哲學家」主張理論化,同時也有某些學者力倡蒐集事實和實驗,相對來說比較沒那麼理論化的實作。又例如,將物理學數學化需要的訓練就與植物學非常不同。另外,天文學該如何研究、什麼才是天文學家該有的信念,也往往有不同看法;被稱為「真科學」的天文學和化學,與被稱為「偽科學」的占星學與煉金術之間的爭議極多;不同實作者對於「自然研究」的範疇,也有相當不同的理解。這真的一點都不誇張。在這些爭議下被建構出來的「科學革命」,其概念下的文化實作也不見得完全能對應現代早期或十七世紀所指涉的科學範疇。歷史學家對於哪些實作才是科學革命的「核心」有不同看法;而當時的參與者對於何種實作生產出的是純正的知識,哪些已經經過徹底改造,也多有爭論。
更根本的判斷標準是,我們應該理解到十七世紀的「大部分人」──甚至是大部分受過教育的人──並不相信專業實作者所相信的,也不認為解釋世界的方式發生了劃時代的革命。如果有人寫了一本完整論述十七世紀自然思想的歷史,卻一點沒提及傳統裡所謂的科學革命,也一點都不令人驚訝。
科學革命這個概念至少表現出「我們」對自己祖先的興趣,這裡「我們」是指的是二十世紀晚期的科學家,他們認為自己所相信的,就是自然的真理;而這樣的關注足以成為我們撰寫科學革命歷史的第二個正當理由。科學史家長期以來都對「當代取向」(presented-oriented)的歷史頗有微詞,認為當代取向的歷史往往自以為是地解釋過去發生的事。但是我們也沒有必要因為這樣就放棄瞭解人類如何從過去走到現在、誰是我們的祖先、我們與過去有什麼樣的連結。在這層意義下,針對十七世紀科學革命的歷史寫作可以詮釋這些轉變──當然,絕對不是直接或簡化地──這些轉變形成當代的某些特色,又因為某些特別的目的,我們也對這些特色感到興趣。科學革命的故事,就如同達爾文演化論中講述人類起源的生命之樹之於整個人類歷史的意義,我們不需要預設這樣的故事能完全解釋幾億年前的生命樣態。細數科學革命的歷史沒有錯,只是我們仍然必須注意,不要給予過分的詮釋。過度聚焦前人先行者的角色並無法合理解釋過去發生的事,因為伽利略、笛卡兒或波以耳並不是典型的十七世紀義大利人、法國人或英國人;提到他們時若只強調他們那些今日已廣被接受的理論,例如自由落體定律、彩虹的光學原理、或理想氣體定律,我們就不可能真正掌握得住他們的專業與研究項目在十七世紀的意義和重要性。
過去並不是在某一瞬間突然變成「現代世界」,這表示如果我們發現十七世紀的科學實作者既具備現代元素,同時也保有傳統色彩時,不應該過於驚訝;他們的觀念需要透過幾代的轉化與改變,才會成為今天的「我們」。而且最終,當我們說著前人,或是這個一脈相承的傳統一開始的故事時,所提到的那些人、那些思想、那些實作,總是反映出某些當代的興趣。我們在伽利略、笛卡兒和牛頓的故事裡,反映了二十世紀末的科學信念,以及我們對這些信念的評價。我們可以基於不同的目的,將現代世界的某些部分追溯回被伽利略、波以耳、笛卡兒和牛頓「擊敗」的哲學家身上,找出一套與現在認可的科學先賢所提出非常不同的,關於自然的知識與看法。我們甚至可以證明十七世紀大部分的人並沒有聽過那些現在被我們景仰傳頌的科學先賢;當時人們所相信的,可能與被我們「挑選出來」的科學前輩所相信的非常不同。再者,十七世紀大多數的人並不住在歐洲,並不知道他們正活在「十七世紀」,也沒有意識到有一場科學革命正在發生。有一半的歐洲人是女人,她們幾乎沒有參與科學文化;大部分的歐洲人(包括男人和女人)若不是文盲,就是沒有接受過正規教育,無法加入科學革命的行列。
摘文
自然與目的:科學世界裡的祕境
這本描述科學革命之作有個一以貫之的主題,就是現代論實作者對於以目的論來詮釋自然現象(也就是把自然效果的目的當成是它的成因)的猜疑,甚至是強烈的排斥;從伽利略與霍布斯對於亞里斯多德學派「自然位置」的批評開始,到梅森以機械論取代「文藝復興時期的自然主義」,再到波以耳對於用哲學性的語言使用「自然定律」的慎重。我們可能會想要下一個簡化的結論,認為這個主題捕捉了科學革命的「本質」,或至少是機械論自然哲學的本質:機械論詮釋就這樣取代目的論詮釋,而現代性就此形成。
但是之前的篇幅卻正好說明了,這樣的結論是不正確的。非常多的十七世紀實作者意識到機械論的詮釋範圍是有限的。自然哲學家的言語可能是機械論的,擱置了所有的目的性,但即便如此,能夠以機械論加以詮釋的,也不見得就等同於世界上的所有現象。其他的實作者雖然也同樣折服於機械論的詮釋價值,卻不認為自然哲學家在提供關於世界的敘述時會有這樣的限制。一方面,笛卡兒設想了一個上帝可能創造的假想世界,一個完全禁得起機械論詮釋的世界:這就是自然哲學家需要去解釋的世界。另一方面,如波以耳及雷(John Ray)這些作家的關切則在於,追尋上帝在祂所真正創造的世界中的意圖及設計。這就是為何他們覺得,當自然界中的證據夠清楚,以目的性來詮釋世界,在哲學上是合宜的。構成「自然神學」基石的設計論證就是在這個意義上成為一個目的論詮釋:它以神聖的意圖來解釋自然構造如何適應其功能。這些在詮釋策略上的差異反映出了,關於「什麼是自然哲學家與自然史學家的正經事」之不同看法。所有的實作者可能會原則上同意,改革後的自然知識應該要消除疑慮、確保正確的信念,並保障維持道德秩序所需的基礎;但他們對於該如何架構自然研究,使其適於從事這些任務上則意見分歧。
對部分哲學家來說,對自然的認知裡會有一個適當的位置留給非機械論及目的論詮釋。在這種情況下,我們不該說機械論是「不完全的」,因為這可能影射了自然哲學家的工作只有提供機械論詮釋,無論那是何種自然現象,或是否有足夠的證據支持這樣的詮釋。比方說,波以耳便為最終成因的哲學適當性提供了一個深思熟慮的辯護,特別是在(但不完全是)詮釋生命體時:「我們所知的自然界中的一切,動物的身體結構可能是最適合以最終成因來加以解釋的。」生命結構的高度複雜性,加上其結構明顯地適應其功能,這些都迫使我們相信存在著一位「理性的管理者」。我們或許可以說,複雜及適應是藉由機械方法而發生的,但卻無法說它們的出現與具知性的設計無關。
到了十七世紀末、十八世紀初,牛頓爵士(Sir Isaac Newton),他有時被稱頌是將機械論哲學帶到完美境界的哲學家,表達了其對於全面提供機械論詮釋的哲學感到不耐。如第一章所示,牛頓並不願意指明重力的機械論成因,同樣的情況也出現在他關於磁力、電力,以及生命現象的處理方法。是誰決定自然哲學的工作定義就是提供明確的機械論成因說明?如果這是自然現象所顯明的,為什麼不使用吸引力或排斥力這種「主動的力」?這樣做不必然就是回到亞里斯多德學派,或文藝復興時期神祕論的談法:「我所探討的這些原理,並不是那種由特定事物歸結來的神祕特性,而是自然的普遍定律,事物因此形成;藉由現象,它們的真實得以顯現,雖然它們成因尚未被發現。這些是明顯的特質,只有其成因才是神祕的。」這不是哲學,而是在我們的感知及智力尚無法確切發現成因假說時,「捏造出」(或以想像調製出)的假說,即使(特別)是那些機械論成因的假說。牛頓寫道,「關於物體,我們能看見的只有其特徵及顏色,能聽到的只有聲音,能碰觸到的只有外部表面,能聞到的只有氣味,能嚐到的只有滋味;但物體內部的物質並不是我們的感知或我們心靈的內省所能瞭解的。」如果其他的實作者將適當的自然哲學等同於提供機械論說明,在此,牛頓則表明了他滿足於自然最終的不可解。應該要認清,知性的適當侷限。自然哲學會是塊堅固而確定的岩石,但其四周則為巨大的神祕海洋所環繞。
前述的討論透露出,在十七世紀的現代論者中,笛卡兒一直是最積極樂觀的機械論成因詮釋提供者,因此與波以耳及牛頓這樣的哲學家成對比;要瞭解笛卡兒在機械論上的野心,他如何看待生命現象(包括人體之運作)是最好的途徑。藉此我們將可以同時深入瞭解,那用來說明人類及人類經驗在現代自然定位的機械論架構,其說明的侷限,以及架構所可能產生的後果。
第一章曾簡單地介紹了,笛卡兒將人類身體解釋為一座「雕像,一座泥塑的機器」。他有意將人類身體的運作全部放在機械論哲學的架構下處理:食物的消化、吸收與排泄;血液的構成,以及它經由靜脈與動脈的移動;呼吸的動作與功能;以及「反射動作」的模式7。當然,構成人體的機械「在組成上是無可匹敵的完美」,勝過那些人類工匠的手藝,儘管如此,那仍舊是一台機器。如此,要解釋人體的運作就可以套用風靡現代早期貴族社會之精巧自動機的說明:擁有隱藏的彈簧、齒輪、輪子,可移動身軀的,甚至還可以發聲的塑像。要承認是機械成因推動這些自動機械之運動毫無困難(畢竟,這是人類所造的),對笛卡兒來說,要以類似的機械論語彙來解釋動物身體的各個面向也同樣沒問題。在笛卡兒看來,物質機械論足以解釋關於猴子或蜜蜂的一切。
然而,對於人類來說,機械論能說明的範圍就侷限得多。對笛卡兒來說,解釋人類身體不同於解釋人類,因為光是從身體構造以及動作並無法完全說明人類的一切。我們並不覺得自己是機器,而笛卡兒也同意我們並不是機器。我們可感受自己運用意志、擁有目的、因著目的移動身體、擁有知覺、進行道德判斷、從事思考及推理(也就是說,會思考),並會用語言表達思考的結論;這些都是笛卡兒認為機械或動物無法做的事情。
人類之所以擁有這些特質並從事這些行為,是由於人類的二元本質:若只考慮其身體,那當然就只與物質的移動相關,但他們還擁有心靈,而心靈的現象最終是無法用物質的移動加以解釋。這個世界本身包含了兩種不同性質的領域,物質的與心靈的。唯有在人類身上,這兩個領域才會互相交會。人類是上帝生命造物中唯一具有「理性靈魂」的。這靈魂是上帝給予的特殊天賦,將人類連結至其創造者,也將笛卡兒哲學連結至聖經。每一個人類靈魂都是由上帝特別打造;它是不朽的;不同於物質、不占空間,也無法分割。於是,這個十七世紀最具雄心的機械論詮釋計畫,最後也終歸於神祕。
這神祕所關切的,是心靈與物質如何在人類架構中會合。我們可以找到一些類似這種神祕結合的例子,像是石頭與重力的結合,手指與手的結合,同一身體裡不同組織的結合等等;但到最後,發生在人類身上心靈與物質的結合才是最根本的,也因此是無法分析的概念。如果說,心靈不占據空間,那它到底在哪裡?這兩個領域在何處相會?這裡,笛卡兒的確提供了一個可能的解釋。正如同所有的知覺及感覺都必須同時是思考的作用物,因此我們所要找的,是一個位於大腦內部中央,一個非左右對稱的小器官(圖30)。那便是小小的松果體,「想像與常識棲身之所」,確實的「靈魂的所在地」。體積微小且僅為周遭血管所支撐的松果體,非常適於從事傳遞心靈與身體的動作。這最終的神祕很恰當地落腳在一個點上。
笛卡兒將他的機械論詮釋計畫推展到可能的極限,最後卻結束於一個位於其機械論哲學範圍之外的概念上,這個概念看來甚至違反了一些他最關切的原理。人類的獨特性來自於,分別位於機械論架構內外之概念的神祕交會。人類擁有具目的性的心靈,而且最後到底還是這個心靈移動了物質。就像你翻開這本書的同時,便顯示了心靈在自然中的角色。如同機械論同時受到宗教敏感度以及人類生活經驗所限,對於人類中心主義的拒否(如第一章所提)也因為機械論無法完全解釋「什麼是人類」而受限。如我們所見,其他自然哲學家們在劃定機械論詮釋範圍的界線時,都較笛卡兒來得小心謹慎;而笛卡兒的說法也常遭受質疑,被謠傳為會危害教會所認可的人類的精神本質,及其與上帝間的獨特關係。然而笛卡兒野心勃勃的機械論計畫並未否定人類在自然世界中所占據的獨特中心位置,只是提供了另一個語法來理解之。神祕的人類本質所身處的那個小點,也就是人類中心主義繼續存在的地方。人類在自然中的特殊位置,既是問題的解答,也是個需要回答的問題,是科學革命留給它文化繼承人的遺產。
書籍代號:0GGK0249
商品條碼EAN:9789865727383
ISBN:9789865727383
印刷:黑白
頁數:304
裝訂:平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