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者:黃芳田
出版品牌:八旗文化
出版日期:2017-05-04
產品編號:978986942319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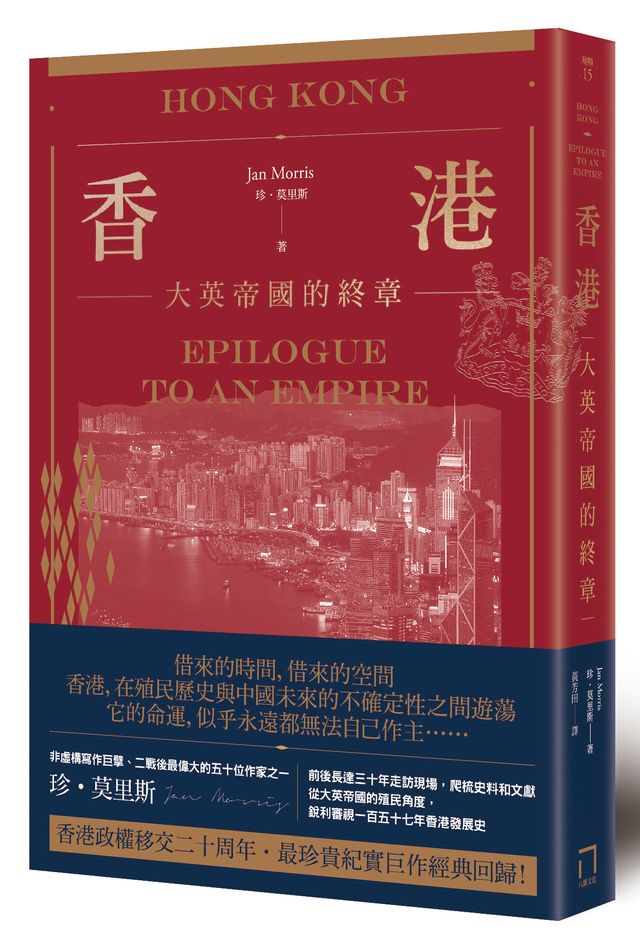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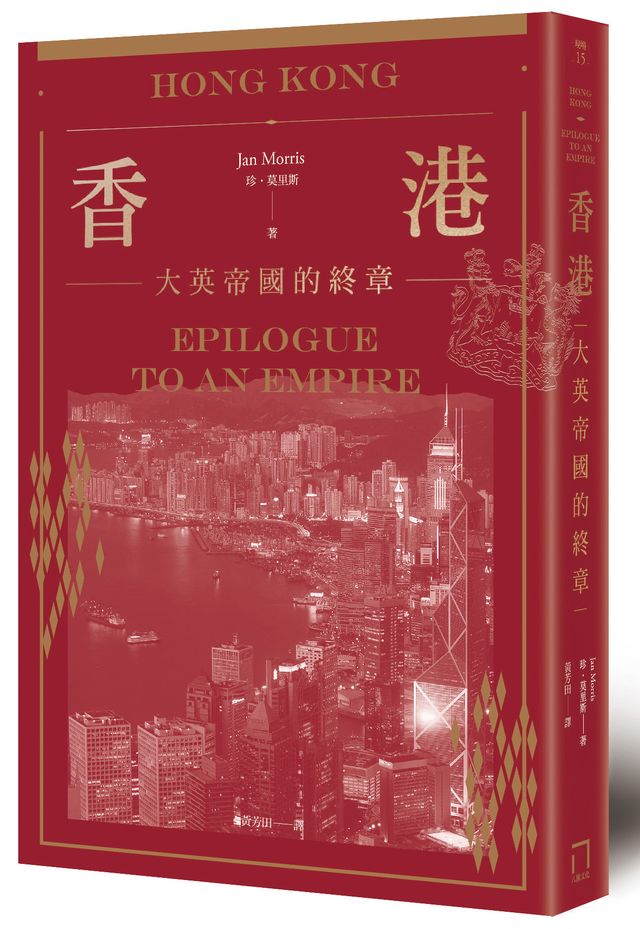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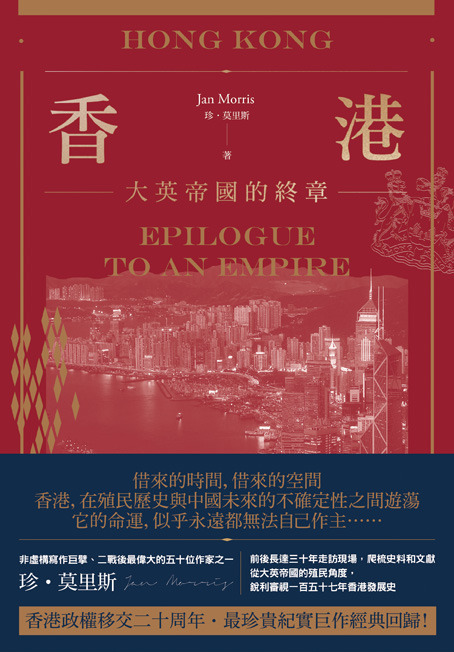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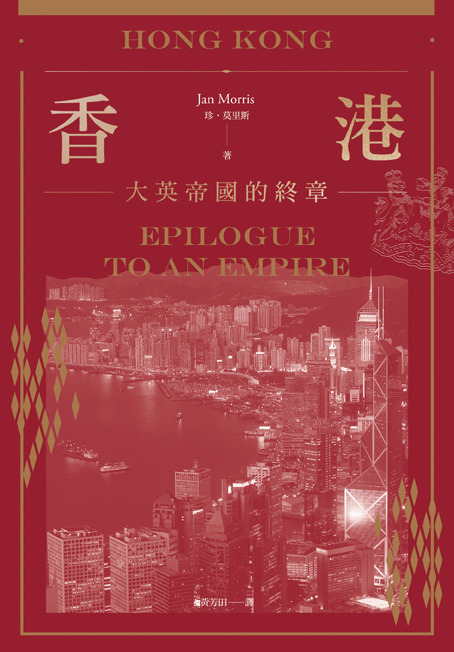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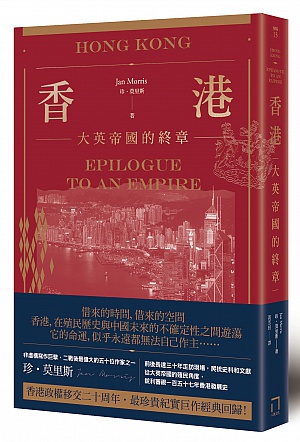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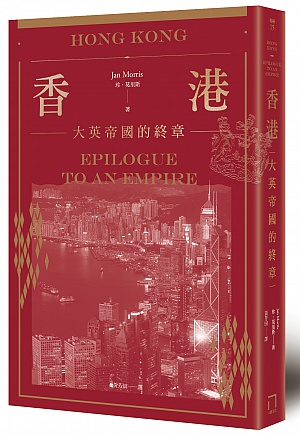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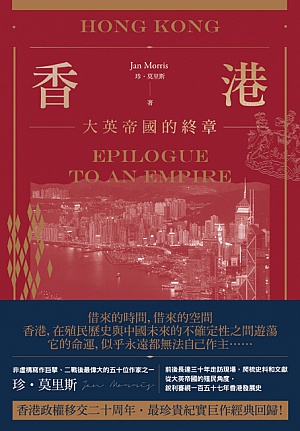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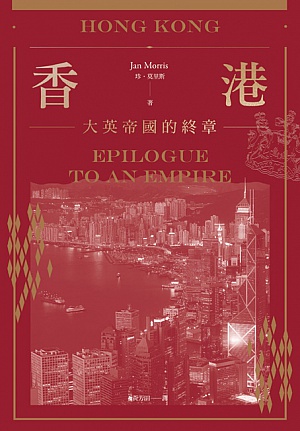
「作者描繪了一座帶有悲劇性格、在殖民歷史與中國未來的不確定性之間遊蕩的城市。她記錄了香港的矛盾和瘋狂,宛如一部充滿戲劇張力的紀錄片。」──《華盛頓郵報》(Washington Post)
香港自一八四二年從大清割讓給英國,至一九九七年政權移交給中國為止,有長達一百五十多年的時間處於獨特的時空背景下,正是這樣的機緣,使它從最邊緣的海島漁村躋身為遠東金融大港,看似與英國親密,卻也始終脫離不了中國的羈絆。
本書寫成於一九九七年香港政權轉移前,被譽為追探香港發展史最經典的報導寫作。作者珍.莫里斯採用雙線敘事,一邊穿插親身見聞,一邊探尋當地的歷史變革,最有特色之處便在於,作者以大英帝國的角度和香港「局外人」的身分現身書中,觀察香港與中國、英國密不可分的關係。
香港在每個階段的變遷都與中國的內部動亂有關,同時也被動盪不定的國際局勢左右,而生活在當地的政商名流、妓女、海盜更影響著香港的社會發展。作者以老練精湛的筆法描繪了這座華洋雜處的城市、它的不同發展階段的各種形象;固然它與英國的關係更貼近,但實際上,這個大英帝國的殖民地從來不曾真正脫離過中國,從來不曾失去骨子裡的華化之感。
既然香港最終要與大英帝國分道揚鑣,那麼,英國最後還能為自己的最後一塊殖民地留下些什麼,足以讓後世來評價呢?這便是作者寫作本書最重要的初衷,也因此使得作者在一九九七年之前,再一次來到香港,記錄下了殖民帝國的最後一頁。
在本書出版二十周年、香港政權轉移二十周年及自身發生了巨大變化的當下,更值得以此書檢視這座偉大的城市──沒有了英國,香港究竟走向一條怎樣的路?而作者在本書終章裡對香港未來的可能發展,在二十年後恰如預言般精準,讓讀者留下深刻的省思。
「作者雙線描繪了香港從小殖民地到繁榮耀眼的過往今昔,並且忠實地為大英帝國最後一個殖民地做了最後一年的記錄與見證,她的成績令人讚嘆。」
──《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
「編年的寫法巧妙,銳利的目光道出一切細節,清楚捕捉了該地的感覺。」
──《舊金山紀事報》(San Francisco Chronicle)
珍‧莫里斯(Jan Morris)
原名詹姆斯.莫里斯(James Morris),一九二六年出生於英國,畢業於牛津大學。一九七二年透過變性手術「成為」珍.莫里斯。曾擔任《泰晤士報》與《衛報》海外特派記者,身兼詩人、小說家、歷史學家、旅遊文學作家等多重身分,獲頒威爾斯大學榮譽文學博士,並被《泰唔士報》譽為二戰後最偉大的五十名作家之一。
珍.莫里斯著作等身,出版作品橫跨各種文體。著有:《大不列顛和平》(Pax Britannica)三部曲、《威尼斯》、《牛津》、《西班牙》、《曼哈頓一九四五》、《雪梨》、《第里雅斯特和不知名之地的意義》(Trieste and the Meaning of Nowhere)、《哈佛的最後來信》(Last letters from Hav)與描述變性心路歷程的自傳《複雜的難題》(Conundrum)、《一個糾纏不清人生之樂趣》(Pleasures of a Tangled Life)等。作品曾獲英國布克文學獎(Booker Prize)、海涅曼圖書獎(Heinemann Award)、亞瑟.克拉克獎(Arthur C Clarke Award)等殊榮。
黃芳田
國立師範大學國文系畢業,曾任中學教師、記者、自由撰稿,現從事翻譯與語言教學,定居香港。著有多部旅遊文學,譯作甚豐,包括:《山》、《海》、《樹》、《深夜裡的圖書館》、《三等車票》、《美味關係》等。
◎三不管的城寨◎
直到幾前年,要是你走在機場北面的東頭村道上,這條路剛好過了九龍和新界的界線,你會見到路的右邊有一排建築群,即使以這玄妙之地的標準來看,也屬於很古怪的區域。可以見到一家接著一家牙科密醫診所,玻璃正門朝著大街,櫥窗擺滿了浸泡的膿腫、產生不良影響的智齒圖解、整排咧開的假牙,每家診所櫥窗裡面可以看到有把牙醫診椅,有時在顧客上門之間的空檔那位牙醫就索性自己斜躺在上面,而他那裝飾用的金魚(可以安撫病人緊張情緒),就在他背景處亮著燈光的水族箱裡般旋游著。
香港到處還是有密醫和牙科密醫在執業,不過在此的這些執業者卻有歷史性理由,他們認為這裡是政府的規定以及督察監管不到的範圍,因為東頭村道的路這邊就是從前九龍城寨的城牆處,要是你還記得的話,這就是從前滿清在英國人來到香港之前就已經保有、做為城寨總部的地方,一八九八年新界租讓時,他們仍在此範圍內保有管轄權。
當年他們那時代這裡是有城牆的城寨,一八四七年又特別重修過,以防禦隔海的英國人。城寨有六座敵樓,城牆厚達十五呎,有五百名駐軍和一所衙門,安穩地坐落城寨中央。城寨大砲是黑身紅口,城寨也會有很激烈的場面:有些照片裡可以看到定罪的罪犯跪在城門外,脖子上掛了大牌子,還有皇家海軍逮捕到的海盜在附近海灘上遭衙門斬首的情景。
當英國人把新界拿到手之後,很快就倚仗著《北京條約》上文字含糊處而把九龍的中國官員擺脫掉了,繼之而來法律上的含糊其詞避開正題也一直未能為這城寨地位定案,於是就變成了「三不管」地帶,一般就俗稱它為「城寨」。每次英方提議要拆除這個地方時,中方就提出反對;英國人也從來不把他們常用的市政規定施加在這個地方,到了一九七○年代,據說真正管城寨行政的是三合會。
城寨周圍的香港處在發展之中時,它卻變成了著名的壞蛋安樂窩。英國人因為一直也不很絕對肯定他們對城寨的權利,於是就由得它去,讓它自生自滅。一九三三年,城寨也差點真的就滅掉,只剩下四百居民,到了一九四○年,城寨所有房舍幾乎都拆除了。然而二次大戰之後,它卻驚人地復甦,那時有成千擅自占地而居的人遷居進來,到了一九八○年代末期,估計已有三萬人住在這裡面。
到這時,城寨也不復滿清時代設防城鎮的模樣,城牆全部被日本人拆掉用來做擴建機場的碎石,城寨裡的建築只有幾座是三十年以上歷史的。然而,它予人感覺仍然像是香港裡的飛地,額外的領域,甚至有點很不真實的感覺。這是個很嚇人的貧民窟,沒有任何四輪車輛可以進到這窟裡——因為裡面沒有一條街夠寬的——建築物有些高達十樓或十二樓,交錯密集緊貼在一起,看起來就像龐然大物的石工整體,加上外層交疊的建構、梯子、走道、水管和電纜,而且只能靠發出惡臭的風井來通風。
迷宮般的黑暗巷道從這邊穿透這龐然大物,再從另一面出來,實際上,白天光線根本就射不進來,鬆垮垂懸的電纜吊在低矮天花板上,因濕氣而滴著水,令人驚恐。它就像個地堡,有時似乎只有你一個人,周圍所有的門戶都上了鎖。有時巷子裡突然亮著一家洗衣店或血汗工廠的燈光,還有很響的中國音樂。在這個迷宮一處通風的空間裡矗立著那座古老衙門,是棟低矮的木造建築,用來當學校以及社區中心,讓人感到即使在這時此地也是個緊密交織、團結異常、同聲同氣的社群,完全跟外面那個殖民地分開。香港的公共衛生條例沒有在這裡實施,這裡也不理會火災的風險,唯一強迫須遵守的規定,就是關於建築物的高度——那時候啟德機場的飛機是呼嘯掠過附近建築屋頂的。
中國政府就跟港英政府一樣,對城寨的看法也是模稜兩可含糊不定,他們一方面從未放棄過對城寨範圍裡所擁有的主權,而且不時拿這個做做文章;另一方面他們又覺得要是特別對城寨小題大作的話,很可能反而等於承認英國對香港有完整的權利。這個貧民窟也就繼續保持它怪異的提醒功能,宛若中國在香港的舞台,中國人以微妙的、耐心的、貓與老鼠般的方式,看著這個殖民地的進展。
一九九三年,九龍城寨終於拆除了,中英雙方對它不再持有不同意見,如今在城寨原址上的是座很雅致的中式公園,老衙門仍在,大大修飾過,像座博物館似地位於公園中央。隨著城寨的消失,香港也少了一個古老的驚險刺激地。雖然就我個人經驗,城寨裡的每個人都很和藹可親,後來那幾年香港警察也到裡面巡邏了,但仍然不停警告遊客:為了安全起見,切勿進入這個地方,有時也會見到遊客經過這裡,隔著那些浸泡膿腫窺伺裡面那個毫不引人的活動範圍時,彷彿在享受著一陣時空錯置之感,神秘東方、不可思議中國的最後顫慄。
◎特殊關係◎
我所以說不可思議中國的最後顫慄,是因為理論上起碼一九八四年的中英聯合聲明首次為中英在香港的關係帶來了開誠布公,在那之前,沒有一件事情是直接了當的,而對城寨地位模糊不明確的觀點看法也可視為範例,跟中英雙方對這個殖民地本身所持態度一樣曖昧。
起碼,自從滿清滅亡之後,中方就否認英方有權待在香港,他們堅稱香港和九龍的割讓以及租借新界,全都屬於不平等條約之列,也就是說,外國人以無情的軍事力量趁中國暫時積弱不振的時候很不公平地強迫中國簽下的條約。不平等條約在十九世紀末最盛,當時英、德、法、俄、葡、日都在中國沿海取得了租界,還加上一個美國,在條約口岸以及勢力範圍內享盡所有特權。
儘管英方不斷否認,但事實上無可否認這些條約的確是不平等,中方的確是在壓力之下被迫割讓這些地方的,但卻沒有任何回報。隨著中國的復興,這些外國權利也一項項廢除了,大部分租界都是在兩次大戰之間結束的——英國在一九三○年撒出了威海衛——到了一九四四年,所有在條約口岸的外國權利全部都正式廢除。上海那個國際大租界也在一九四五年告終。到了二十世紀下半葉,中國沿海就只剩下兩個始作俑者的外國飛地:葡萄牙人的澳門,葡萄牙人在這裡已經有四百年了,但因為這地方實在太小,因此幾乎沒有什麼意義,還有就是英國人的香港。
甚至在講到香港(六百四十萬人口)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十二億人口)之間的關係時,都似乎有點滑稽——倒像是成為俘虜的詹遜跟日本帝國的外交關係似的。但是這關係並不僅是一個小殖民地和大國之間的關係而已,而是兩股龐大的歷史力量之間的關係——是兩種文化、傳統、體制、種族和價值觀之間的關係。這是接近其霸權地位鼎盛時期的現代化西方那股無可抗拒的能量,放在中國邊緣這個香港殖民地;也是傳統中國文明的無能跌至谷底時讓這事情發生了;是雙方逐漸趨於平等,加上科技的散播吸收了雙方,現在把這個關聯帶到了高潮結局。
◎香港對中國的提醒與帶頭作用◎
香港面積只有它龐大主體國的九千分之一,經常被喻為中國皮膚上的寄生蟲,有時從太平山頂眺望大陸那邊,可以感受到九龍山區後方就是中國宛若無盡大地的開始之處,這片大地伸向遠方直到西藏或蒙古,在我看來,中國那些領導人眼中的香港必然也不過像是皮膚上惱人的癢處差不多。然而這個明喻卻是不實的。香港的角色從來都不是被動或僅是過度活躍而已;這個殖民地曾經是很多更強大勢力的中介,在跟中國打交道時,它也盡其所能以赴。
它在歷史上大部分時候是具威脅性多過受到威脅;從一開始,它就反抗中國的法律和傳統,無論是跟天朝皇帝有關的或者是在禁止輸出中國技術給外國人方面。它一再成為攻擊中國大陸的基地,並在一八六○年額爾金勛爵侮辱滿清時發揮至極,還有在摧毀北京避暑山莊時。的確,整個十九世紀期間,這個殖民地一直鄙視中國。一八九五年,在中國最慘痛和受辱的這個世紀的末期,據怡和洋行耆紫薇的觀察,他說,「我也難說究竟寬容對待中國會不會對中國是件好事;因為這樣一來它可能會好了瘡疤忘了痛,忘掉了逆境以及至苦帶來的教訓。」無論時局是好是壞,西方一直從香港監測著中國,這個殖民地向來都是針對大陸的諜報與政宣活動基地。今天聳立在這個殖民地空中探測的電子大天線和碟式天線其實都是位於英格蘭喬丁漢的通訊總部的前哨,也是英美遍布全球竊聽系統的部分,其他則是英國廣播公司華語節目的定向天線,用來對這個人民共和國最偏遠的角落廣播的。即使是今天,對中國事務報導最全面的,是在香港的媒體,無論是用中文或英文,很多版面都專門用來報導北京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會議,無數條新聞都留下了紀錄,而這些在人民共和國內卻是永不會見天日的。
在北京或廣州的敵對主權也慣常在這裡,在英國旗幟的掩護下,做他們的顛覆準備功夫;擁護共和政體者對抗滿清,共產黨對抗國民黨,國民黨對抗共產黨。周恩來於一九二七年在香港尋求庇護,那是他在中國興起到掌權過程早期的事;而當時在台灣仍然夢想著反攻大陸的國民黨威權,也向來用香港做為基地,方便他們在南中國搗鬼。很多敗北的軍閥也曾撒退到香港來計畫捲土重來——例如最著名的「將軍」李福林,帶著九名妻妾住在新界一座堅固設防的豪宅裡,過了很多年儼如南面王的奢華生活。
西方帝國主義向來既是發展的工具也是用來剝削的武器,而香港也不斷投射新生命力到奄奄一息的龐大中國去,無論好壞,因為它持續不斷施壓尋求跟中國做生意的管道,而漸漸打開了這個國家,使它走進現代化的現實世界中。即使是鴉片貿易,起碼也指導了華人金融家現代匯兌手法,示範了當代船堅砲利之術的好處,也協助打開了那些滿大人的雙眼,讓他們看清事實:外國人也許是蠻夷,但卻不一定是傻瓜。最初跟香港洋行打交道的仲介,還有後來為洋行服務的華人買辦,是最早批真正的大都會華人之一,同時扮演了啟蒙與貪婪的媒介角色。西方技術也嫁接到東方的基礎上,中國甦醒的第一個象徵是種混合式設計的中國帆船,叫做「火船」,有中國船身和西式索具。
後來香港的商人和銀行家也在中國本身的工業革命上扮演了帶頭角色,雖然成績不過爾爾。他們認為中國正在向西方的輸出開放龐大新市場,還有其廣無比的投資良機。雖然他們免不了要在中國烏煙瘴氣的貪污腐敗、重重障礙、無知和誤解中摸索前進,但仍不斷敦促遲鈍的滿洲威權邁向進步,而香港也不大像讓中國發癢的寄生蟲了,倒像是會螫人的黃蜂,嗡嗡發出鳴聲,不時螫一下這個昏睡巨人,好讓他醒來。
十九世紀的蒸氣工具大部分也是透過香港仲介傳到中國去的。美商旗昌洋行、顛地洋行、怡和洋行以及太古的那些結實堅固的內河汽船成了進入中國內陸的主要交通工具,香港的汽船也主宰了沿海貿易。全中國第一條鐵路是由怡和洋行興建的,這是條古老奇特的窄軌鐵路,銜接上海和吳淞,於一八七六年通車,但並沒有維持很久,滿清政府對於這個開端很排斥,不過這條鐵路卻開啟了龐大的興建鐵路熱潮,這股熱潮讓中國在十九世紀末轉了型。到最後,怡和洋行與香港匯豐銀行組聯營企業,以資助並發展這個系統的大部分,也就理所當然了。
大量金錢從香港注入了大陸,除了投資的金錢之外,中國政府也一再向香港貸款,香港匯豐銀行變成了北京的最大勢力之一。有好幾年中國所有關稅都是直接付給匯豐銀行,而中國在一九三五年放棄銀本位制度時,所有交出給政府的白銀都是儲存在匯豐銀行的地窖裡。軍閥也來到香港來籌款打他們的仗,一九三○年代中國抗日戰爭時,百分之七十的中國軍費是經由這個殖民地轉過去的。
從香港去的工程師協助治理每年的黃河氾濫,中國第一部升降電梯是由怡和洋行安裝的。香港也供電給中國電力網絡,甚至還有過這個小之又小的殖民地協助減輕中國食物短缺的問題。奧曼尼(F. D. Ommanney)一九五○年代住在香港,他就報導過,中國鬧大饑荒時,他的女傭回廣州探親,為那些挨餓的親戚帶過邊境的,包括有兩隻雞、一隻鴨、一包水果、臘腸、雞蛋、茶葉和甜食、大量乾燥大餅以三大袋裝得滿滿的鍋巴,都是從飯鍋底刮下來的。
◎氣壓調節室◎
「神仙洞府」是十九世紀中國學者魏源對香港的形容,中國學者經常以客套與詩意的誇張來表達他們自己,但無疑中國人向來也對香港、香港的精湛技術以及快速的轉變感到驚訝。早在一八四五年有個廣州高官曾經寫了一首稱道這個殖民地的頌詩,形容它是建在岩石上的白色皇城,建築在晨光中閃耀——「然而不久之前此地只見髒亂漁家陋舍,如今安在?——似秋天離去的燕子般消失了!」一八七○年詩人王佐賢(音譯)說這殖民地是「宛若捲入一片樂歌之中,群山酒肉氾濫」。政治家王道(音譯)把它比喻為一行飛雁,而維新政治家康有為則非常推崇這個殖民地的管理策略,曾經寫過「建築壯觀,行行道路井然有序,警察儀表莊嚴……。」
香港曾經是邊界彼端與海岸以北的中國最有力的榜樣,中國見到這個殖民地,就跟見到現代化本身的體現差不多,而這個小殖民地和那龐大共和國之間在物質成就上的強烈對比,也會造成一種激勵——香港平均每二十二人就擁有一輛汽車,中國卻平均每一萬零二百二十人才有一輛!中國在管理技術、建設上,在建築、金融方面,都向香港看齊。電腦時代絕大部分是通過香港才在大陸開展的,外界簽約時不可或缺的公司法概念,本來是共黨中國完全不懂的,也經由香港的法律社群而逐漸滲入了中國。
當初盧押創辦香港大學時,他是有意使之成為中國的一個知識榜樣——一座英國的學海燈塔,光芒照亮四周。香港也一直是基督教傳福音布道者的基地,即使是在毛澤東時代,也照樣經由這個不很基督教文化的殖民地把基督教教義投射到中國去;有個改宗的組織「新生命文學」設有專差帶聖經進大陸,而「中華研究中心」也像之前許多布道團體一樣,因為「許多中國人心靈空虛」的事實而表達了它的關切。
尤其如今在這個人民共和國裡陣陣復甦的資本主義意識形態,也在香港找到了就近的榜樣,幾乎是難以視若無睹。幾百萬共產黨同志都在香港有親戚,其中很多更到過香港見過這地方,話說回來,歷史也證實了中國向來都不曾擺脫過香港模式。當年孫逸仙這個在香港求學的醫學院學生,就是在此地醞釀出那些推翻君主專政以及驅逐天朝王國、終而建立起強國地位的種種想法。有段時間因為認為他會危及香港的太平以及良好秩序,所以禁止他入境香港,但二十五年之後,他卻在香港大學告訴一群聽眾說:他的革命靈感就是來自於香港本身——他深深受這個殖民地井然有序的平靜與安全保障所影響,比較起來,五十哩之外位於廣東省的家鄉卻處於失序和沒有安全保障中。「兩個政府相異之處令我印象深刻……。」
我想,大概除了最民智未開或最偏遠地方的鄉下人之外,其他所有中國人都知道香港,它是擴及全世界各大小華人社群的大中華圈中的大都會,這個非正式的遼闊帝國裡每個角落都跟這個殖民地有親友或經濟上的聯繫,匯往大陸家鄉的款項是經由香港轉寄的,大中華圈的國民也經常途經香港進出大陸,於是香港成了候見室,或者更該說是氣壓調節室,大中華的人潮,也就是人民共和國界定的「海外華僑」川流不息經此出入大陸。
有一次我搭乘中國船隻從香港前往上海,發現這船本身完全就是個華人世界的縮影。隨著我們離了香港這門檻進入到大陸範圍之內,船上也像個家庭大團聚似的。船員全部都是人民共和國的國民,開朗、能幹,很樂意為你從船上小吃吧送來一條包在油紙裡瘦巴巴的鴨腿,而你穿過一扇標有「船員專用」字樣的門時,他們也很識相地假裝沒看見。乘客中包括有各種華人,有到海外探完親回來的老年人,有來自台灣和菲律賓的華僑,有香港學生,有貿易任務在身的華裔美籍生意人,還有兩個學院中人,結束了在歐洲的研究回到國內。
整整三天我們的船航行在南中國海上,從來不曾形單影隻過,因為附近總是見得到漁船,而且也很少有看不到沿岸景緻的時候,每次出現地標特色時,乘客就興奮地彼此指點看著。等到航行到了長江口,逆流上溯往上海時,這趟經驗對我更加倍充滿寓意,感到自己像是置身在一群歸家的流浪者之中;但我也感到彷彿隨著所有從香港北航到中國的船隻後浪,重溫了鴉片走私者、運茶葉的飛剪船、太古和怡和洋行的汽船,以及本書中所出現那大批銜接香港與大陸的中國帆船與舢舨所航行過的路線。走筆至此,眺望窗外的香港海港,我依然見到那同一艘船「上海號」,船尾飄著紅旗,正在從駁船上把貨裝載到船上去,準備著下一趟的返國之航。
(節錄自第十一章「地主」)
書籍代號:0URP0015
商品條碼EAN:9789869423199
ISBN:9789869423199
印刷:單色
頁數:400
裝訂:平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