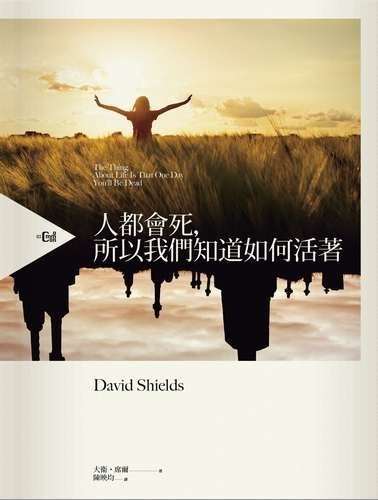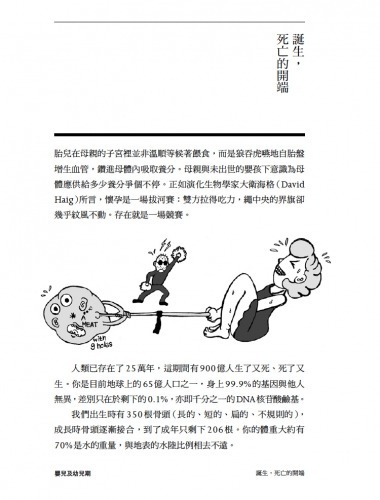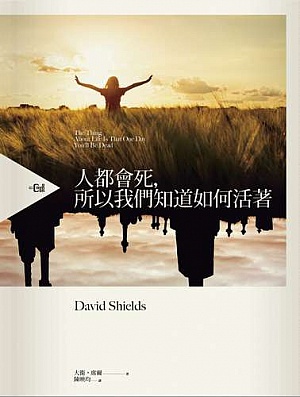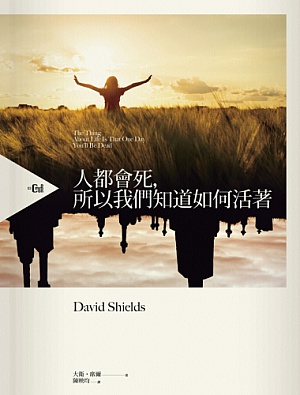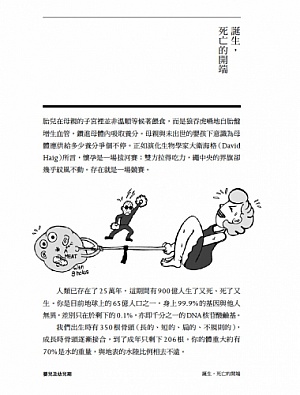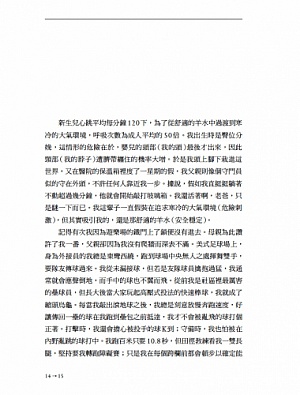內文摘要
誕生,死亡的開端
胎兒在母親的子宮裡並非溫順等候著餵食,而是狼吞虎嚥地自胎盤增生血管,鑽進母體內吸取養分。母親與未出世的嬰孩下意識為母體應供給多少養分爭個不停。正如演化生物學家大衛海格(David Haig)所言,懷孕是一場拔河賽:雙方拉得吃力,繩中央的界旗卻幾乎紋風不動。存在就是一場競賽。
人類已存在了25萬年,這期間有900億人生了又死、死了又生。你是目前地球上的65億人口之一,身上99.9%的基因與他人無異,差別只在於剩下的0.1%,亦即千分之一的DNA核苷酸鹼基。
我們出生時有350 根骨頭(長的、短的、扁的、不規則的),成長時骨頭逐漸接合,到了成年只剩下206 根。你的體重大約有70%是水的重量,與地表的水陸比例相去不遠。
新生兒心跳平均每分鐘120下,為了從舒適的羊水中過渡到寒冷的大氣環境,呼吸次數為成人平均的50倍。我出生時是臀位分娩,這情形的危險在於,嬰兒的頭部(我的頭)最後才出來,因此頸部(我的脖子)遭臍帶纏住的機率大增。於是我頭上腳下栽進這世界,又在醫院的保溫箱裡度了一星期的假,我父親則像個守門員似的守在外頭,不許任何人靠近我一步。據說,假如我直挺挺躺著不動超過幾分鐘,他就會開始敲打玻璃箱。我還活著啊,老爸,只是瞇一下而已。我這輩子一直假裝在追求寒冷的大氣環境(危險刺激),但其實吸引我的,還是那舒適的羊水(安全穩定)。
記得有次我因為遊樂場的鐵門上了鎖便沒有進去。母親為此讚許了我一番,父親卻因為我沒有爬牆而深表不滿。美式足球場上,身為外接員的我總是東彎西繞,跑到球場中央無人之處揮舞雙手,要隊友傳球過來。我從未漏接球,但若是友隊球員擒抱過猛,我通常就會應聲倒地,而手中的球也不翼而飛。從前我是社區裡最厲害的壘球員,但長大後當大家玩起高壓式投法的快速棒球,我就成了縮頭烏龜。每當我敲出滾地球之後,我總是刻意放慢奔跑速度,好讓傳回一壘的球在我跑到壘包之前抵達,我才不會被亂飛的球打個正著。打擊時,我還會擔心被投手的球K到;守備時,我也怕被在內野亂跳的球打中。我跑百米只要10.8秒,但田徑教練看我一雙長腿,堅持要我轉跑障礙賽;只是我在每個跨欄前都會頓步以確定能跨過去,然後也跑了最後一名。我沒學過跳水,每次都是雙腳先入水。於是游泳教練拖我到跳板邊緣,幫我擺好手腳姿勢,再把我舉起來丟到池子裡。但在最後一刻,我別過臉,落水時水花四濺,好像跌進一張鋪滿電針的床。我在怕什麼?為什麼我老是這麼怕痛?
在印度教經典《薄伽梵歌》中,人體是被開了九個洞的傷口。客觀來說,新生兒一點都稱不上美。臉頰沒肉,下顎缺牙齒支撐。頂上若有毛,也細軟得貌似禿頭(白人小孩尤其如此)。嬰兒全身覆蓋一層稱為胎兒皮脂的奶狀物質,可保護嬰兒那發紅、濕潤、皺巴巴的皮膚。通過產道時,擠壓產生的腫脹也可能使嬰兒的鼻子暫時變形、雙眼發腫,或把頭形拉得又長又怪。嬰兒頭骨發育尚未完全,有些地方的骨頭未完全接合,大腦也僅有軟組織保護。嬰兒受母親荷爾蒙的刺激,外生殖器不分性別都大得不成比例,而且乳房也微微腫脹,甚至分泌一種叫做「巫奶」的乳水。嬰兒的虹膜呈淡藍色,眼睛真正的顏色則要長大後才看得出來。頭部占身體比例大半,頸部力道不足以支撐頭部,而臀部極小。
新生兒平均體重為3.3 公斤,身長53 公分。出生後不久,體重會減掉原來的5~8%,主要原因為水分流失。出生後24小時內,在空氣進入耳咽管前幾乎沒有聽力。嬰兒想念子宮,厭惡所有外界的刺激,任何東西一到嘴裡或嘴邊就開始吸吮。眼神散漫又鬥雞,體溫不穩,呼吸不規律。
一個月大的嬰兒能夠搖頭晃腦、舞動四肢。兩個月大的嬰兒,仰躺時可直視前方,趴臥時可抬頭約45度。三個月時,嬰兒的頸部肌肉可支撐頭部一、兩秒鐘。
新生嬰兒的腦部大小是成人的25%,這是由於人類直立行走的機制限制了母親骨盆的尺寸(也就是說,產道不可能更大)。不過嬰兒隨後便迅速彌補了這項限制,1歲前,腦部將長到成人的75%。嬰兒能聽見頻率高達四萬赫茲的聲音,會被高頻的狗哨嚇到,而成人由於無法接收高於兩萬赫茲的聲音,根本不會有感覺。你耳朵內的聽覺髮細胞能將耳蝸內的液體動能轉換為電子訊號,再由神經細胞傳至大腦成為聽覺。到了青春期,這些髮細胞逐漸消失,你開始喪失某些頻率的聽力;首先聽不到的是高頻音。新生兒通常雙手握拳,但若輕敲其虎口,小手會抓緊你,力道之大,在雙手同時緊握時足以支撐全身的重量。這種與生俱來的「抓握反射」對人類嬰兒沒多大用處,但若回到演化史的前一個時期,這種反射卻是生死攸關,讓猿人嬰兒得以攀附於母親的毛髮上。
父親提醒我,根據猶太法典《米德拉西》(Midrash,一本經長時間編修而成的希伯來聖經注釋),你來到這個世界時,雙手緊握,好像在說:「一切都是我的,我將繼承所有。」離開這世界時,你鬆開雙手,好似在說:「我什麼都不帶走。」嬰兒要是不小心墜落了,原先的蜷曲姿勢會在瞬間四肢大開。
這樣的「驚嚇反射」(或「擁抱反射」),能讓嬰兒盡可能伸展全身,方便人猿母親接住墜落的孩子。
娜塔莉出生時我哭了,但妻子蘿莉一滴淚也沒掉—她沒空。前一分鐘我們還在候診室裡手牽著手翻閱雜誌,下一分鐘,蘿莉看著我,以從所未見的嚴肅表情命令道:「放下雜誌。」 娜塔莉蹦了出來,咂叭咂叭舔著嘴唇,我還著急地向護士確認那並非糖尿病的徵兆(我親子教養手冊看太多了)。我向老天發誓,我再也不會計較芝麻綠豆的小事,不再有愚蠢自私的想法;這樣崇高的境界沒有持續很久,不過……
印第安的科吉族人相信,嬰兒在生命初始時,只認得三件事:母親、夜晚與水。
詩人湯普森(Francis Thompson)寫道:「我們在他人的苦痛中誕生,/在自身的苦痛中消殞。」楊格(Edward Young)寫下:「誕生不過是死亡的開端。」培根 (Fracis Bacon)說:「除了哭喊,我們還剩下什麼?/哭喊著不要出生、不要在出生中邁向死亡?」納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的《說吧,記憶》(Speak, Memory),開章第一句話便寫道:「搖籃在深淵上擺盪。常識使我們明白:存在不過是一道倏忽的光線,閃耀於兩端永恆的黑暗之間。」
生死一線間,是個老掉牙卻極少受到討論的話題。1919年,9歲的父親和一群朋友在布魯克林區信步穿越鐵軌。他走在最後,卻不小心一腳踩上供電軌,於是一個活蹦亂跳的孩子霎時成了電流的「倒」體。火車隆隆駛向我父親米爾頓.席爾卡特(Milton Shildcrout),而他軟綿綿地倒在地上,沒法制止自感電流通過身上。(我問過父親為何改姓,他說:「二戰時有個中士,軍營裡每日佈告上的字只要超過兩個音節他就不會念,也無法正確念出他所謂『該死的紐約姓氏』。中士以他濃得化不開的南方口音說道:『下士啊,你的名字太長了,哪天咱們出海外任務,你挨了日本鬼子的子彈,墓碑都寫不下咧!你該把姓名縮短,讓咱們這些大人念得出來。從今天起,俺要叫你席爾斯。』幾週後,這位中士又把我的姓縮短為席爾,我就席爾席爾地在么陸肆軍區待了36個月,後來也習慣了,退役回家後乾脆把姓氏給改了。」)
我今天能坐在這裡打這行字,要感謝一名身穿黑衣、頭戴紫帽,名做大艾的17歲摔角選手。他見狀伸出一枝乾木柴,將電昏的小米爾與供電軌分開,趕在火車駛來前一刻把他拉出鐵軌。我父親不但被電得手肘膝蓋瘀青,後來那個夏天更成了行屍走肉,皮膚由紅轉粉紅又轉黑,最後更脫皮見骨,手指與腳趾甲碎裂,僅剩的毛髮一一脫落,直到連小米爾也幾乎消失無形。後來爺爺向長島鐵路索賠一百美金,結果拿到不多不少正好一百美金的醫藥費,作為他每週一次到醫院檢查傷口是否感染的補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