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者:李靜宜
出版品牌:木馬文化
出版日期:2017-03-29
產品編號:97898635936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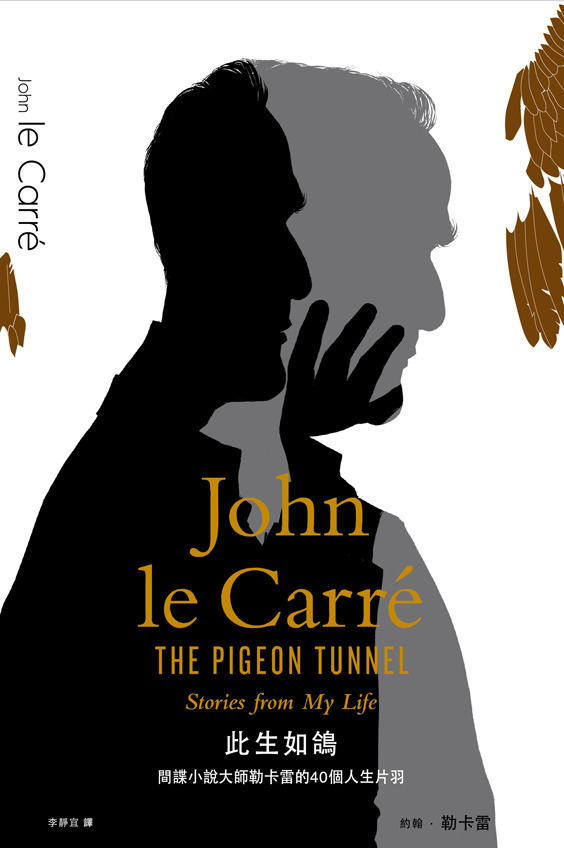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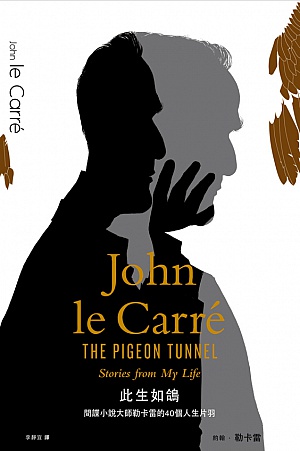
間諜小說大師勒卡雷的唯一自傳
☆《冷戰諜魂》裡利馬斯、《榮譽學生》中的傑里•威斯特貝……令人難忘的悲劇英雄經典角色的原型
☆《女鼓手》中的以巴對抗、《蘇聯司》裡蘇聯的改革開放……故事靈感來源與取材經過
☆勒卡雷與諾貝爾文學獎最近的距離
☆接觸戰地、戰地記者、反抗軍、恐怖分子、情報頭子的實際親身經歷
☆間諜小說的真實與虛構……
所謂愛國與叛國的一線之隔,間諜任務與作家的良心拉扯,盡在其中。
——嚴格來說它甚至不像一本自傳,至少不是你我想像中那種、從童年經驗娓娓道來,一直講述到他如何踏進又離開英國情報單位、如何靠著寫作功成名就的制式自傳。
在全書的38個章節,如果加上序和前言的話,勒卡雷約莫就是訴說了人生中最令他印象深刻、影響他寫作至深的40段經歷——
比方與戰地記者大衛•葛林威溜進烽火漫天的金邊(間諜小說家說這是他第一次真實感到子彈從頭上飛過),在那裡大衛/勒卡雷結識了英勇的法國女子伊薇特•皮耶波利,她與情人在金邊開運輸公司,平常用飛機運毒品或寶石,戰時偷渡烽火孤兒出來並為他們向法國領事館申請庇護——他們全是她生的孩子,都是法國人,她堅稱——這段經歷提供了他《榮譽學生》裡的一個角色、一段場景,伊薇特的人生則催生了他動人的《永遠的園丁》女主角。
諸如此類的故事,有些令人感到驚奇、不可思議,有些令人潸然淚下或呀然失笑——訪談遭美國刑求關押、最後無罪開釋,與《頭號要犯》男主角命運相似的所謂「伊斯蘭恐怖分子」、親眼直擊《使命曲》裡非洲軍閥角力真實情況、《蘇聯司》裡俄羅斯改革開放經驗的觸發……作家的生命與經歷,和他關注的戰爭、歷史重疊;倘若他的小說是真實世界不為人知、黑暗的那一面,他的自傳便是真實人生與黑暗世界的灰色重疊。
40段經歷中,勒卡雷無可避免地以頗具分量的篇幅寫下了他的童年——他身為騙徒的父親、感情冷漠的母親——
「逃避與欺騙是我童年非有不可的武器。青少年時期,我們都是某種間諜,而我卻早已是退役的老兵。情報世界擁我入懷的時候,感覺就像回到家一樣。」
——首度談到自己對世紀間諜金•費爾比的看法;他諸多個性鮮明、設定生動的角色來源,他的小說改編成電視電影的經歷,與好萊塢知名演員、導演、編劇打過的交道……
「格雷安‧葛林告訴我們,童年是作家的存款簿。若以此來計算,我生來就是個百萬富翁。」
——這次,我們終於有機會看到文學界的百萬富翁與成功企業家,向世人分享他最珍貴的財富。
約翰‧勒卡雷(John Le Carré)
生於一九三一,離開伯恩及牛津大學後,於冷戰期間於伊頓公學教書、服務於英國外交部,並在英國情報局任職的五年間寫下《死亡預約》、《上流謀殺》及他的第一本全球暢銷小說《冷戰諜魂》——被譽為二十世紀最了不起的小說之一。這三部小說塑造了喬治‧史邁利一角,他也出現在《鏡子戰爭》一書,也是「卡拉」三部曲:《鍋匠‧裁縫‧士兵‧間諜》、《榮譽學生》與《史邁利人馬》的主角。過去五十五年他靠寫作維生,將自己的人生劃分為倫敦市與康瓦爾郡兩個時期。
約翰.勒卡雷最近出版的小說包括二○○八年《頭號要犯》(A Most Wanted Man)、二○一○年《我輩叛徒》(Our Kind of Traitor)以及二○一三年的《脆弱的真相》。
勒卡雷一生得獎無數,包括一九六五年美國推理作家協會的愛倫坡大獎、一九六四年獲得英國毛姆獎、James Tait Black紀念獎等,一九八八年更獲頒CWA終身成就獎(另分別在一九六三與七七年獲頒金匕首獎),以及義大利Malaparte Prize等等。至今已出版的二十三部作品,不僅受到全球各大媒體的矚目與讀者的歡迎,更因充滿戲劇元素與張力,已有十九部被改編為電影與電視劇。
李靜宜
國立政治大學外交系畢業,國立政治大學外交研究所博士,美國史丹福大學訪問學者。曾任職出版社與外交部。譯有《理查費曼》、《諾貝爾女科學家》、《牛頓打棒球》(牛頓)、《現代方舟二十五年》(大樹),《古烏伏手卷》、《法律悲劇》、《古典音樂一○一》、《直覺》、《奇想之年》(遠流)、《追風箏的孩子》、《史邁利的人馬》、《遠山的回音》(木馬)等。
序
我坐在瑞士小農舍地下室的書桌前。這幢房子是我用《冷戰諜魂》賺來的錢蓋的,坐落在距離伯恩九十分鐘火車車程的小山村。十六歲那年,我逃離英國公學,就是來到伯恩,在伯恩大學註冊入學的。每逢周末,我們一大群學生,有男生有女生,但大半是伯恩本地人,全湧到這裡來,擠在山區小屋裡,滑雪滑到快掛掉。就我所知,我們都非常純潔正直,嚴守分際:男生一邊,女生另一邊,從來沒有人出雙入對。就算有,我也從來沒見到就是了。
農舍位在小村上方。透過窗戶,仰頭上望,我就會看見艾格峰,僧侶峰和少女峰,以及最漂亮的西爾伯峰和略矮一點的小西爾伯峰:這兩座尖尖的可愛冰頂每隔一段固定的時間,就會在名之為「焚風」的溫暖南風吹拂下變成黑色,但幾天之後就又恢復新娘般的聖潔光輝。
這裡有不少守護神,包括無所不在的作曲家孟德爾頌——可以跟著孟德爾頌步道的箭頭走——詩人歌德,雖然他好像最遠只走到勞德本納的瀑布;還有詩人拜倫,他一路走到威根納爾普,但很討厭這個地方,說我們這爿受風暴肆虐的森林「讓我想起我自己和我的家人。」
但是我們最愛戴的守護神,無疑是恩斯特‧蓋茨。他在一九三○年創辦勞伯峰滑雪賽,自己並贏得滑雪障礙賽,為小山村帶來了名氣與財富。我有一回昏了頭竟跑去參賽,結果因為實力不足與完全掩飾不了的恐懼,一如預期,摔個重跤。根據我的研究,恩斯特不甘於只當滑雪賽之父,他還為我們的滑雪屐裝上鐵邊,給我們的皮靴固定裝置加上鋼板,我們或許都應該為此感謝他。
時值五月,所以我們在一個星期之內體驗了四季:昨天下了六、七十公分的新雪,沒有半個滑雪者去暢快一滑;今天驕陽當空直射,雪幾乎全融了,春天的花朵開始忙著登場。然而到了近晚的此刻,暗灰色的雷雨雲已經準備好要像拿破崙的大軍團那樣揮軍直擣勞德本納谷地。
而在雷雨之後,過去幾天放我們一馬的焚風很可能就會捲土重來,天空、草地和樹林都霎時色彩褪盡,農舍開始吱吱嘎嘎,煩躁不安,柴煙滾滾從壁爐冒出來,熏黑我們的地毯。這條地毯是不知哪一年沒有降雪的冬季,某個雨天的午後我們在茵因拉肯用太貴的價錢買下的。從山谷傳來的每一個噹啷轟隆聲,都響亮得像示威者的忿怒嘶吼。所有的鳥在這段期間都躲在鳥巢裡,只有誰都不甩的紅嘴山鴉例外。焚風來襲,別開車,別求婚。要是你頭痛,或一心想殺了你的鄰居,請放心,這不是宿醉,是焚風作祟。
這幢農舍雖然很小,在我八十四年的生命裡卻占有不成比例的極大分量。還沒蓋這幢農舍的很多年之前,我還是個年輕人,經常來到這個山村,先是滑雪,穿上梣木或山胡桃木做的滑雪屐、套上止滑帶爬上坡,然後用真皮的皮靴固定裝置滑下山。後來是在夏天的時候,和我那位博學睿智的牛津導師維維安.葛林一起在山間散步。後來出任林肯學院院長的維維安也是我描繪喬治.史邁利內心世界的原型。
史邁利和維維安一樣喜歡瑞士的阿爾卑斯山,像維維安一樣在這片風景裡找到慰藉,或者和我自己一樣,與靈感來源的德國有長達一輩子、始終糾纏難解的關係,都不是巧合。
容忍我叨叨絮絮講著我那任性無常的父親羅尼的是維維安;在羅尼又一次上演更加誇張的破產大戲之後,想辦法籌足現金讓我完成學業的,也是維維安。
在伯恩,我認識了伯恩高地最古老的旅館業主後裔,若非他後來所發揮的影響力,我一開始根本就不可能獲准蓋這幢農舍,因為當時就和現在一樣,外國人在這個山村裡,連一米土地都不准擁有。
也是在伯恩的時候,我開始在英國情報界踏出如嬰兒學步的第一步,傳送我不知道是什麼的情報給我不知道是誰的人。近來,我常空下來的時候就尋思,當初我如果沒有逃離公學,或者如果闖向另一個方向,我的人生會如何呢。如今想來不免震驚,我人生後來發生的種種,都起因於當年一個莽撞幼稚的決定。我當時一心只想著以最快也最可行的方法離開英國,擁抱德國當我的代理母親。
我並非在學校表現不佳,恰恰相反:我是很多活動的隊長、校內競賽的優勝者,前途似錦的未來金童。而我的出走極其低調。我沒咆哮怒吼,只說:「父親,隨便你想拿我怎麼辦,橫豎我是不會再回去了。」我十之八九是把自己的悲慘遭遇怪到學校頭上——順便連英國一起怪罪——但真正的動機卻是不計一切代價逃離父親的掌控,而這是我無法對他明說的。後來,我也看著自己的孩子做同樣的事情,只不過他們做得更漂亮,更不帶火藥味。
但這些都無法回答最主要的問題,也就是當年若非如此,我的人生會走上哪一個方向?沒有伯恩,我還會被英國情報單位招募去當跑腿小弟,做著行內所謂的「東一點西一點」的工作嗎?當時我還沒讀過毛姆的《祕密情報員》,但當然讀過吉卜林的《基姆》,以及諸如亨提之流作家所寫的許多愛國歷險小說。唐佛德‧葉茲、約翰‧卜強和萊特‧哈葛德說的怎麼可能有錯。
當然,在大戰結束僅僅四年之際,我堪稱西半球最愛國的英國人。唸大學預科的時候,我們男生個個是專家,都知道怎麼從我們之中揪出德國間諜來,我甚至還參加了一個格外厲害的反間諜行動。在我們那所公學,愛國的狂熱奔放無度。我們一個星期上兩次軍訓——是穿上全套軍裝的軍事訓練。我們的年輕老師都剛從大戰歸來,皮膚曬得黝黑,每到軍訓日就穿戴全部的勳章。我的德文老師參與了一場不可思議的神祕戰爭。生涯規劃老師讓我們作好心理準備,要到大英帝國的遙遠前哨基地去奉獻終生。我們那座小鎮市中心的修道院掛滿在印度、南非和蘇丹等殖民地戰場被砲彈撕裂的國旗碎片,而這些碎布後來經由可愛的女性之手織成魚網,重現榮光。
所以,當偉大召喚化身為英國駐伯恩大使館簽證組這位名喚溫蒂的三十多歲媽媽型女士出現在面前時,不自量力在外國大學唸書的這個十七歲英國男學生當然馬上立正,說:「聽候您的差遣,女士!」
比較難以解釋的是,在「德國」這兩個字對許多人來說等同無比邪惡的那個年代,我竟然全心全意擁抱德國文學。然而,就像我出逃伯恩一樣,對德國文學的擁抱,決定了我此後的人生。若非如此,我不會因為我那位猶太難民老師的堅持,而在一九四九年造訪德國,親眼看見魯爾區那些被夷平的城市,然後病得像條狗似的躺在柏林地下鐵德國臨時野戰醫院的國防軍舊床墊上;我也不會在營舍臭味未散之時親訪達豪與柏根貝爾森的集中營,然後回到伯恩平靜祥和的生活裡,繼續擁抱我的湯瑪斯‧曼與赫曼‧赫塞。我也絕對不會被派到盟軍占領的奧地利服國民役,從事情報工作,之後也不會到牛津研習德國文學與語言,到伊頓任教,以低階外交人員的身分為掩護,派駐波昂的英國大使館,更不會寫出以德國為主題的小說。
早年沉迷於德國事物所帶來的正面影響,如今已昭然若揭。這讓我可以打造屬於自己、不拘一格的疆域,讓我成為無可藥救的浪漫主義者,愛上抒情的表現方式;在我心中種下深信不移的想法,知道從生到死的人生旅程就是永無止境的教育學習——這個概念不知道是打哪裡來的,而且大概也頗值得質疑,但這個想法就是根深柢固。後來開始讀歌德、藍茲、席勒、克萊斯特、畢希納的戲劇時,我發現我不只有他們典型的嚴肅自勵,也有他們的神經過度緊張,而且兩者等量齊觀。在我看來,絕竅就是拿這兩個特質來彼此掩護。
☆
農舍已近五十高齡。孩子們成長的階段,每年冬季都來這裡滑雪,我們在這裡共度過最美好的時光。有時候我們春天也來。也是在這裡,我想是一九六七年冬天吧,我和薛尼∙波拉克 度過與世隔絕,但歡樂無比的四個星期。波拉克是電影導演,導過《窈窕淑男》、《遠離非洲》,以及我最愛的《射馬記》。當時我們正在研究把我的小說《德國小鎮》改編為電影劇本。
那年冬季的雪下得極好。薛尼從沒滑過雪,也是第一次到瑞士。看著快樂的滑雪人滿不在乎地從我們的陽台外呼嘯而過,實在讓他受不了。他也想加入他們,而且一刻也不能等。他要我教他,但是老天保佑,我打電話叫了馬丁•艾普來。馬丁是滑雪教練,也是傳奇的登山嚮導,是世上僅有的幾個獨自登上艾格峰北坡的人之一。
來自美國印第安納州南灣市的A咖導演,和出身瑞士阿羅薩的A咖登山者一拍即合。薛尼做什事情都不半調子,不出幾天的工夫,就已經滑得很好了。他滿心熾熱期望,想為馬丁‧艾普拍一部電影,而且這個念頭很快就凌駕想拍《德國小鎮》的欲望了。艾格峰將是電影裡的命運之神。我來寫劇本,馬丁演自己,薛尼則綁上安全束帶,爬到艾格峰半山腰去拍攝馬丁的鏡頭。他打電話給他的經紀人,把馬丁的事情告訴他。他打電話給他的分析師,把馬丁的事情告訴他。雪還是極好,繼續消耗薛尼的精力。
我們覺得晚上洗過澡之後是最佳的寫作時間。但無論這個想法到底對不對,最後兩部電影終究都沒拍成。
後來,讓我有點意外的,薛尼把農舍借給來為電影《飛魂谷》勘景的勞勃‧瑞福。唉,我沒見過他,但是此後許多年,只要我到村裡來,都像身上戴了個「勞勃‧瑞福之友」的胸章。
☆
這都是我回憶裡的真實故事——你們有權利質問,到底哪一些是真相,而哪一些又是我們這些潛心創作的作家在美其名為人生黃昏的此刻所回想起來的回憶呢?對律師來說,真相是未經修飾的事實。至於這些事實是不是能被挖掘出來,則是另一回事。對從事創作的作家來說,事實是素材,不是控制他怎麼做的工頭,而只是他的工具。他的任務就是讓這些素材奏出樂聲。如果有所謂的真相可言,真正的真相並不在於事實本身,而在於其間的微妙差異。
真的有「純粹的回憶」這種東西嗎?我很懷疑。就算我們堅信自己冷靜客觀、忠於赤裸的事實,絕不出於自利而增刪修改,純粹的回憶仍然滑溜如香皂,無法掌握。至少對我——一輩子都在編織融合經驗與想像力的我——來說,確實是如此。
每回想到值得一提的故事,我就會從當年在報刊上發表的文章裡挖出一段對話或陳述,因為如今讀來依舊津津有味,新鮮得很,況且隨著時日推移,回憶已經無法呈現同樣鮮明的意象:例如,我對前KGB首腦瓦汀‧巴卡廷的描述。也有些情況,我保留了當年所寫下的故事原貌,只稍微整理一下,或稍加潤飾,讓情節更清晰或更合時一些。
我不希望讀者以為可以藉此深入瞭解我的作品——或者有任何的瞭解,因而期待讀到一些零星解釋的段落。但是請放心:我絕對沒有刻意偽造扭曲任何事件或故事。略作掩飾確有必要沒錯,但偽造扭曲,絕對不必。只要回憶裡有任何不確定之處,我都會特別述明。日前有一本談論我人生的書出版,其中約略提及了一、兩則故事,但都只有片麟半爪,所以我當然很樂於自己再談一遍,用我自己的聲音述說,也竭盡可能注入我自己的情感。
有些事情我在當時並不瞭解其中的重要性,後來很可能因為某位主角的離世才意識到。在漫長的人生裡,我沒有寫日記的習慣,只有偶爾寫寫旅行筆記,或記下幾行此生難再有的對話:例如,我在巴勒斯坦解放組織主席阿拉法特被逐出黎巴嫩之前,與他的會面。之後,我到突尼斯他住的白色旅館拜訪他,卻沒能如願,又隔幾個星期,就在這個小城,駐紮在同一條馬路幾哩之外的數位巴解高級將領,遭以色列暗殺小組狙殺。
擁有權力的人,無論男女,都很吸引我,因為他們就活生生在我們面前,而且我很想知道他們的動力到底是什麼。可是事後回想,在他們面前我都只是似有見地的點頭,適時搖頭,想辦法擠出一、兩個笑話化解緊張。一直要到會面結束,回到飯店房間之後,我才掏出我那亂七八糟的筆記本,努力把方才聽到、看到的一切理出個頭緒。
其他在旅行裡保存下來的潦草筆記,大部分都不是我個人的記事,而是我闖蕩江湖時陪在我身邊保護的那些虛構角色寫的。這些筆記都是以他們的角度,用他們的筆法來書寫,而非我角度、我的筆法。那次我蜷縮在湄公河畔的掩蔽壕裡,這輩子頭一次聽見子彈飛射進頭頂上方的土堤時,用顫抖的手在骯髒的筆記本上吐露憤慨之情的並不是我,而是我那位勇氣十足的虛構英雄,戰地記者傑里—威斯特貝 。對他來說,被子彈擊中只過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我始終以為只有我是這樣的,但後來我認識一位知名的戰地攝影記者,他告訴我說,只有透過鏡頭,他才能擺脫恐懼。
呃,我從來都沒能擺脫恐懼。但是我瞭解他的意思。
☆
如果你運氣夠好,在寫作生涯剛起步就贏得成功,就像我當年出版《冷戰諜魂》那樣,你這輩子就會簡單分成「墮落前」和「墮落後」兩個階段。回頭去看你還沒被探照燈逮著之前寫的書,讀起來就像你天真無邪年代的作品;而之後的書,若處於低潮,簡直像是面對審判時的苦苦奮戰。「太過用力了。」書評家大聲說。我從來不覺得自己太過用力。我覺得為了成功,必須竭力把自己最好的東西表現出來,而且整體而言,不管這所謂的「最好」到底是優是劣,都是我努力的成果。
而且我熱愛寫作。我喜歡做我此時此刻正在做的事:烏雲密布的五月清晨,躲在窄仄的書桌振筆疾書,山雨順著窗戶倉皇奔落,沒有理由撐起傘蹣跚走到火車站去,因為《紐約時報國際版》要到午餐時間才會送到。
我喜歡邊走邊寫,散步的時候,搭火車或泡咖啡館的時候,寫在筆記本上,然後快快回家,檢視自己的戰利品。在漢普斯德的時候,石南園裡有張我最喜歡的長凳,窩在枝繁葉茂的樹下,遠離其他的座椅,我很愛坐在那裡寫東西。一直以來,我只用手寫。這麼說或許很傲慢,但我偏愛這已經流傳千秋萬世的非機械化書寫傳統。我身上這個怠惰已久的繪畫藝術家真的很享受塗畫文字的樂趣。
我最喜歡的是寫作的隱密性,這也是我之所以不參加文學節活動的原因,而且只要可能,我就不接受專訪,雖然從過往的紀錄來看好像也並非如此。有時候,通常都是在夜裡,我會後悔莫及,恨不得自己從沒接受過任何訪談。你先是創造了自己,接著,又相信了你所創造的。這和自知之明簡直是背道而馳。
進行研究之旅的時候,我或多或少可以因為真實人生裡的另一個名字而得到保護。在旅館簽名的時候,我可以毫不擔心是不是會有人認出我的名字:而沒有人認出來的時候,我又苦惱尋思是為什麼。若是碰到我希望能借用經驗的人,不得不如實招認自己的身分時,後果也大不相同。有人會不肯再給我分毫信任,但也有人會把我捧上天,當我是情報組織的頭頭,我反駁說我只做過最低階的情報工作,他的回答卻是你當然會這麼說囉,不是嗎?然後不斷給我許多我不想要、不能用,聽過也就不記得的告白,只因為誤以為我可以代為轉達給某個「我們知道是誰」的人。這種既好笑又傷神的困境,我碰到過好幾次。
但是在過去五十年裡,被我這樣騷擾過的可憐人——從製藥企業的中階行政主管到銀行員、傭兵,以及各形各色、程度不一的間諜——大部分都對我表現出極大的耐心與寬容。而最寬大為懷的莫過於戰地記者和國外特派記者,他們保護著寄生蟲也似的小說家,相信他擁有他其實並沒有的勇氣,還允許他如影隨形。
如果沒有大衛‧葛林威的忠告與陪伴,我簡直無法想像自己如何完成在東南亞與中東的短暫訪問。葛林威是《時代雜誌》、《華盛頓郵報》與《波士頓世界報》戰功彪炳的東南亞特派員。膽小的新手想搭上他的便車簡直是天方夜譚。一九七五年一個下雪的早晨,我們在這幢農舍一起吃早餐,享受暫時離開前線的片刻休息。就在這時,他接到華盛頓辦公室打來的電話,說被圍困的金邊馬上就要淪陷落入赤棉手中。從我們的這座山村並沒有馬路可以下山,只能搭小火車去轉搭較大的火車,然後再換搭更大的火車,輾轉到蘇黎士機場。轉瞬之間,他已經從一身阿爾卑斯山的裝束換成戰地記者的粗衫布衣和舊韖皮鞋,和妻女吻別,迅速走下山坡到車站去。我也快步追著他,因為他的護照在我手上。
葛林威舉世聞名,因為他是最後一位降落在被圍困的美國駐金邊大使館屋頂的美國記者。一九八一年,我在連接約旦和西岸的阿倫比橋 得了痢疾,葛林威粗暴地帶我穿過等待通關的大批煩躁旅客,憑藉純粹的意志力,以三寸不爛之舌讓我們得以通過檢查哨,送我過橋。
重讀我對一些事件的描述時,發現不知是因為太過於自我中心,或是刻意想讓故事顯得更鮮明生動,我隱去了當時也在場的其他人不提。
我想起和俄國物理學家,也是政治犯的安德烈•沙卡諾夫與他的夫人葉蓮娜•邦納在餐館裡談話的往事。那天在當時還叫列寧格勒的城市裡,「人權觀察組織」為保護我們,派了三名成員與我們共桌,一起忍受KGB的幼稚干擾——他們派出一隊人馬裝作攝影記者,在我們附近繞來繞去、手上舊式的圓球形相機鎂光燈不停對著我們的臉猛閃光。我很希望當天在場的其他人也在別的地方留下他們自己對那歷史性一天的記錄。
我回想起雙面諜金•費爾比的多年同事與好友尼可拉斯•艾略特端著一杯白蘭地,在我倫敦家裡的客廳昂首闊步。我後來才想起,內人當時也在場,坐在我對面的扶手椅,和我一樣被他給迷住。
就在寫出這段回憶的同時,我想起那天晚上艾略特帶著妻子伊麗莎白來吃晚飯,受邀的還有一位我們很喜歡的伊朗客人。這位朋友講得一口完美的英文,只稍稍有一點點甚至顯得頗有魅力的瑕疵。這位伊朗客人離開之後,伊麗莎白轉身,眼睛發亮,非常興奮地對尼可拉斯說:
「你有沒有注意到他有點口吃耶,親愛的?和金一樣!」
關於我父親羅尼的冗長故事會擺在本書的後面,而不是開頭的篇章,因為我不想讓他如其所願地又強行搶占了故事的鋒芒。儘管我花了許多功夫在他身上,他卻跟我母親一樣在我心中仍舊成謎。除非特別指明,否則書中所有情節都是新寫就的。如有必要,我也會改換名字;主角或許過世了,但他的後人和繼承人可能無法理解箇中幽默。我嘗試條理分明地梳理自己的人生,就算不是編年紀事,也盡量以主題分類;不過也跟人生一樣,路愈變愈寬,到後來就不連貫,也難有條理了。有些故事最後只能呈現出它們在我心中的樣貌:純粹的意外,不需多加解釋,沒有任何特殊意義,只是反映出我心裡的想法,因為它們讓我警惕、恐懼或感動,讓我在半夜突然醒來,讓我哈哈大笑。
隨著歲月流轉,我所描述的某些際遇,在我眼中彷彿成了一小段從「犯罪當場」捕捉到的歷史,我想年紀較大的人都會有這種感覺。通篇重讀,從鬧劇到悲劇,再從悲劇到鬧劇,我覺得有點不太可靠,但不確定是為什麼。或許讓我覺得不可靠的其實是我自己的人生。但是事到如今,再要做什麼都來不及了。
☆
有很多事情我從來不願意寫,每個人的人生裡必定都有這樣的事情。我有過兩位忠於婚姻、摯愛奉獻的妻子,對於她們,我有無盡的感謝,也有很多的歉意。我始終不是模範丈夫與模範父親,也向來不想表現得像。我很晚才懂得愛,在經過多次失足之後才懂。我沒給自己的四個兒子作好道德示範。至於我在英國情報單位的工作(主要都是在德國執行),已經有其他人在其他地方發表過基本上並不正確的描述,我也不希望再添加任何說法。這一方面是基於我對自己服務過的單位還有著老派的忠貞態度,另一方面也是因為對於願意與我合作的女士先生們,我曾有過承諾。我們之間達成的共識是,保密的約定沒有期限,將延續到他們的兒女及其他後代。我們進行的工作既不危險,也不戲劇化,但對投身其中的人來說,卻包含了痛苦的自我反省。無論這些人如今是不是還在世,保密的承諾依舊未變。
間諜這個工作,可以說是從出生以來就對我有莫大的吸引力,一如大海之於福瑞瑟,或印度之於保羅•史考特。我以一度熟知的祕密世界為藍本,試著為我們所棲身的這個更為廣闊的世界創造一個大劇場。最初源自於想像,接著尋找實境。然後再回到想像,最後來到我此刻俯首疾書的書桌。
書籍代號:0EJC0024
商品條碼EAN:9789863593621
ISBN:9789863593621
印刷:單色
頁數:400
裝訂:精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