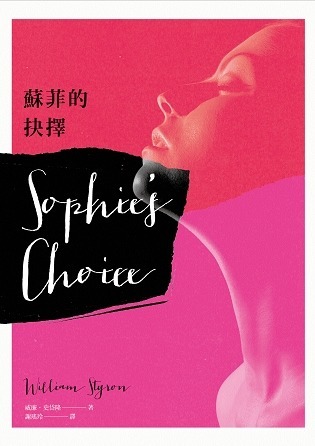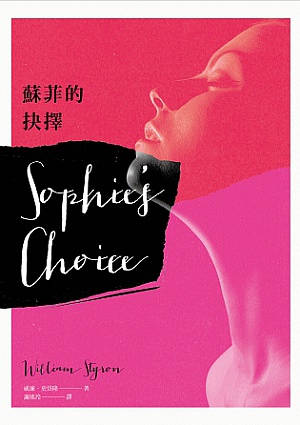她知道必須迅速採取行動,否則一旦被抓就完了。她按捺住狂跳的心,側身走進房間,步伐不穩地走了最後幾步,立即,她察覺到出了錯誤,在計策及時間上犯了致命的錯:當她把手放到收音機冰涼表面的那一刻,她便有種災難的直覺,像無聲的叫喊般充滿了整個房間。後來她不只一次回想當她碰觸那渴望已久的小東西的一剎那,她心中回想起,很久以前在花園裡聽到父親輕蔑地說:妳從沒有做對過一件事情。但她剛想起這句話的當兒,便聽到另一個冷靜的聲音由背後傳來:「妳的職務只讓妳在樓梯上上下下,這房裡可沒妳的事。」蘇菲隨即轉過身子,瞪視著愛咪。
那女孩站在衣櫥前,蘇菲從沒有在這麼近的距離看過她。她穿著淺藍色的內褲,早熟的胸部束在同色的胸罩內。她的臉既白又圓,像塊沒烤熟的餅,圈著鬈鬈的黃髮;她的五官漂亮但平坦,眼睛、鼻子、嘴巴看起來像是被畫在──蘇菲最初認為像畫在一個洋娃娃上,繼而又覺得像畫在汽球上。蘇菲瞪著她,心想:爸爸說的對,我總是弄糟每件事情;進到這個房間前竟沒有先看看是否有人。她好不容易才張口說道:「對不起,小姐,我只是──」但愛咪打斷了她的話。「用不著解釋。妳是進來偷收音機的。我親眼看見的。我看見妳想把它拿起來。」愛咪臉上毫無表情。她雖近於全裸,卻神色自若地探手從衣櫥裡拉出一件白色法蘭絨袍子穿上,然後轉過身來,得理不饒人地說:「我要告訴我父親。他會處罰妳。」
「我只是看一看!」蘇菲辯稱道:「我發誓!我經過這裡好多次。我從來沒有看過這麼……這麼小的收音機。而且又這麼……這麼精巧!我真不相信它真的可以用。我只是想看看──」
「妳說謊,」愛咪說:「妳是想偷它。從妳的表情我就看得出來了。妳看起來就是想偷它,而不只是拿起來看看。」
「妳一定要相信我。」蘇菲的喉嚨已湧上鯁塊,全身虛弱疲乏,雙腿又重又冷。「我不會拿妳的……」但是她停住口,覺得這已無關緊要。她愚蠢地把工作弄砸了,再也沒什麼要緊的了。她所在乎的只有第二天與兒子的會晤,愛咪怎麼可以阻礙他們母子重逢?
「妳想偷它,」愛咪咄咄逼人。「這值得七十馬克。妳可以偷到地窖去聽音樂。妳是個髒波蘭仔,波蘭仔都是賊。我媽說波蘭仔比吉普賽人的手腳更不乾淨,也更髒。」那張圓臉上的鼻子皺了皺。「妳好臭!」
蘇菲的眼前一片黑。她聽到自己的呻吟聲。由於壓力或飢餓或哀傷或恐懼,天知道究竟怎麼回事,她的月經已經遲了一個禮拜(她來到集中營後,曾有過兩次這種情形),然而此刻她卻覺得有股血流了出來,同時她眼前的黑暗逐漸擴大。愛咪白皙的臉漸漸陷在黑暗的網中,蘇菲發現自己跌落,跌落……在時間緩慢的波浪中浮沉,她聽到遠處傳來一種叫囂聲,逐漸增大,最後成為一聲野蠻的怒吼。模糊的剎那間,她夢見那是發自一隻北極熊的吼聲,而她躺在冰山上,被寒風吹襲。她的鼻孔燒灼得厲害。
「醒醒。」愛咪說。她那張白蠟似的臉靠得很近,蘇菲的面頰可以感受到她的呼氣。蘇菲這才意識到自己倒臥在地板上,而那孩子蹲在她身旁,拿著一瓶阿摩尼亞在她鼻子下揮動。玻璃窗是開的,冷風直入室內。她所聽到的尖叫是集中營的哨音;此刻她再度聽到那遙遠的聲音。愛咪膝蓋旁放著一個塑膠藥箱子,上面畫了一個綠色十字。「妳昏倒了。」愛咪說:「別動。先讓頭部保持水平,好讓血液流動。深呼吸。冷空氣會使妳復甦。靜靜地躺一下。」蘇菲的記憶逐漸恢復,覺得自己像是演出一齣主要場幕已經消逝的戲:才不過是一、兩分鐘前(不可能已過了很久),這孩子不是還對她忿然責問嗎?此刻竟然像個天使般照顧她?是她的昏厥激起了這個小惡魔的護士心腸嗎?蘇菲不安地呻吟著之時,這個問題得到了解答。「妳要好好躺著,不要動!」愛咪命令她:「我上過急救課。妳照我的話做,明白嗎?」
蘇菲靜靜躺著。她沒有穿內衣褲,不知道她的血染了多大的範圍。她的罩衫背部似乎濕透了。在這種情況下她為自己的細心感到驚異,同時她也想到她是否沾污了愛咪乾淨的地板。這孩子的態度使她更覺無助,也有一種既被服侍也被試驗的感覺。
愛咪熟練地輕拍蘇菲的臉頰,終於使她的臉恢復了一點血色,然後愛咪命令她的病人坐起身靠著床畔。蘇菲聽從了她的指示,慢慢坐起身,突然為她在這要命的一刻昏倒滿懷感激。因為此刻她望著天花板,瞳孔逐漸恢復正常,愛咪已經站起身,以一種頗為寬容的好奇瞪著她看,似乎驅除了對蘇菲既是個波蘭仔又是個賊的怨憤。「我要說一件事,」愛咪喃喃說道:「妳真的很漂亮。衛菡敏說妳一定是瑞典人。」
「告訴我,」蘇菲以一種溫和而熱切,近於哄騙的聲音說:「告訴我,繡在妳袍子上的那個花樣是什麼?好可愛。」
「那是我游泳冠軍的勳章。我是我們那班的冠軍。初級班。那時候我才八歲。真希望這裡也有游泳比賽,可惜沒有。都是戰爭的緣故。我得在梭拉河裡游泳,可是我不喜歡。河裡有好多垃圾。我在初級班比賽時游得好快。」
「那是在那裡舉行的呢,愛咪?」
「在達丘。我們要塞的孩子有個很棒的游泳池。池水還是溫的。但那是在我們被調到這裡來以前的事。達丘比奧許維茲好多了。不過,那是在德國境內。看我那些銀杯。中間那個最大的。那是童軍團團長親自頒發的。妳看看我的剪貼簿。」
她從衣櫃抽屜中拿出一本很大很大的相簿,露出剪報和照片。她把相簿抱到蘇菲身旁,先停下腳步扭開收音機。吱吱喳喳的聲音騷擾了原本寧靜的房間。她調了一下,雜音消失了,換上號角和喇叭響亮的合奏聲。愛咪翻出一大堆照片,指著穿泳裝的她,一再地說:「那就是我。」蘇菲望著照片,不舒服地想著:達丘也有陽光嗎?「我也開始學潛水,」愛咪說:「妳看,這就是我。」
蘇菲不再看那些照片──那全都變得模糊一片──她轉而望向敞開的窗子外,寶藍的十月天空,明星晶瑩閃爍一如水晶。空氣中有股騷動,光線突然增強,一捲捲的煙隨著涼爽的晚風襲來。這是蘇菲自早晨以來第一次聞到燒人肉的氣味。柏肯諾正在焚燒最後一批來自希臘的猶太人。喇叭!用喇叭演奏的讚美樂曲飄向窗外──使得蘇菲想起明天即將來到的早晨。她開始哭泣,提高聲音說:「至少我明天會見到傑恩。至少。」
愛咪問:「妳為什麼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