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者:張家綺
出版品牌:八旗文化
出版日期:2017-09-06
產品編號:978986951684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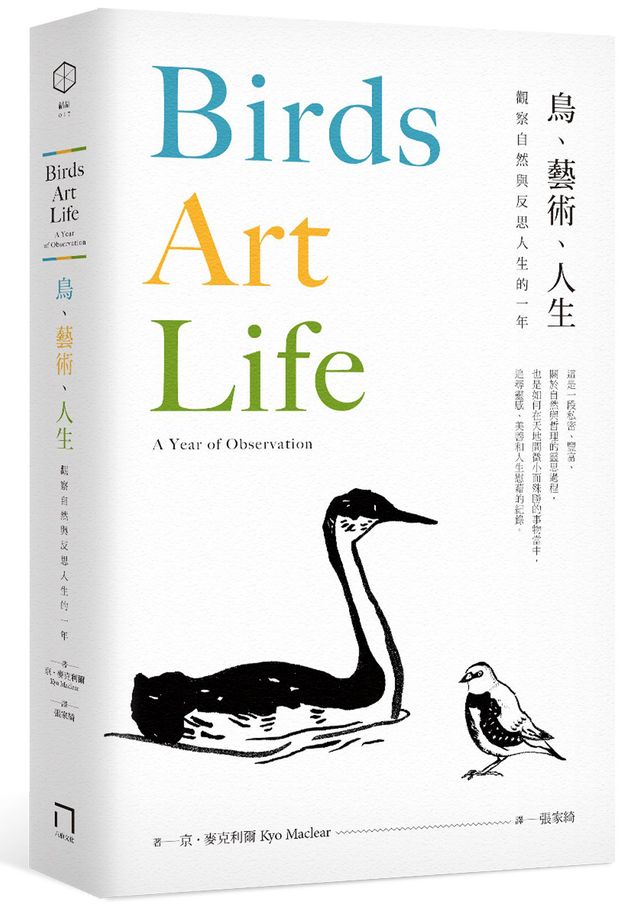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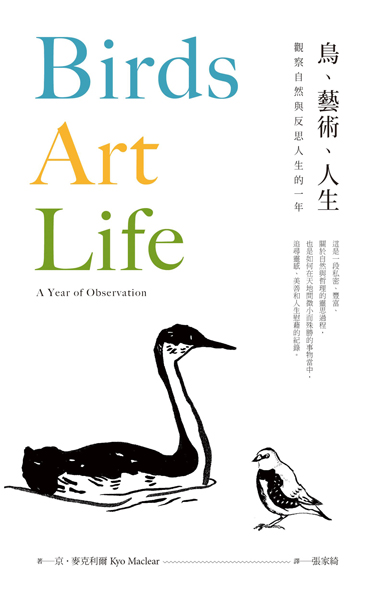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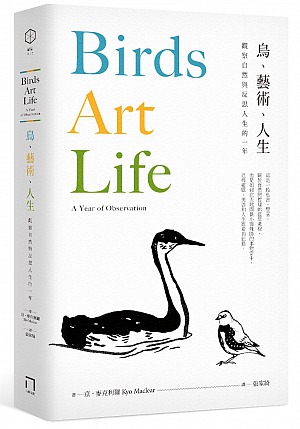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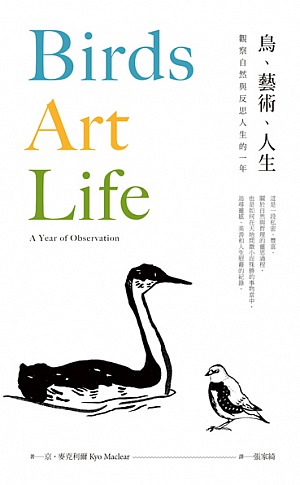
穿梭在細看與宏觀之間,凝視內心世界和外在自然,這段對鳥兒和生活的觀察年記,以四季流轉和人生遭遇為節奏,探觸每個人在生命中必然會經歷的愛、等待、寂寞、失落、圓滿,或者遺憾。
麥克利爾因為父親的病情和終將到來的告別而哀傷,她因緣際會遇見一位剛愛上觀察鳥類的音樂家。她好奇,是什麼驅使一名年輕音樂家突然間擁抱自然,在多倫多這座城市裡熱切追逐鳥兒的蹤影?
她決定跟隨這位音樂家的腳步,一探究竟,卻意外展開一段串連起自然與心靈的啟示之旅。
觀察城市裡鳥兒的羽色體態和啾啁啼囀,她發現,若打開眼與耳去感受自然,竟能得到何等的啟發與靈感。而在這過程中對於人生悲喜的反思,雖是她對生命中的起伏與疑惑的感受及解答,但深層裡尋問的,仍是關於人類在天地間的定位,自我與他人的連結,以及自然和藝術當中的美與善如何引領我們窺見生命的意義。
歷經四季,照見內在心緒和外在世界,游移裡外,串聯起細微與宏大,這段兩位藝術家相遇後造就而生的觀鳥紀錄,安靜而有力地引人思索創造與自然的本質,以及人生核心問題當中的微妙奧義。
•「她的細想與靈思,能讓讀者享受在自然書寫中尋找紛雜世界的意義。」—Booklist
•「簡練與精準底下暗藏深度,這本書好似海上冰山,而麥克利爾刻意略隱在後的,正建構出冰山的完整全貌。」—Kirkus Reviews
•「節奏優美,陳述簡潔,以行雲流水般的神韻,觸探人生的核心問題。本書誘人之處,正在於當中對城市裡自然界微物的細膩觀察,反思人在大自然韻律中的存在定位,以及探索人生的束縛與自由之間的關係。」—Publishers Weekly
京・麥克利爾Kyo Maclear
小說、散文作家,同時也創作童書。英國倫敦出生,四歲隨英籍記者父親與日籍水墨畫家母親遷居加拿大。多倫多大學藝術及藝術史學士,文化研究碩士,目前正以加拿大政府獎學金,在多倫多約克大學進行博士研究。麥克利爾的散文及評論常見於北美、歐洲、亞澳地區的報刊媒體,除寫作外亦有繪畫長才,本書中所有插畫即是她親自繪製。
張家綺
畢業於中興大學外國語文學系,英國新堡大學筆譯研究所,現任專職譯者,譯作十餘部。
【序言】
有天早上,我站在咖啡店的櫃台前,凝視著正為我煮咖啡的男子那雙粗厚的濃眉。我發現,你若是無意再度陷入愛河,就不該久久凝望一張臉。當我望見咖啡機冒出的熱氣在他的眼鏡上覆滿蒸氣,當我看到他在霧氣後瞇著眼、為我的咖啡拉花時,一股愛意襲捲了我。人臉具有一種近乎不宜直視的親暱感,在一個萬物終究將毀壞的世界裡尤其如此。我們很難任憑自己觀看,卻不牽引出情感的後果。
這個男人跟我一樣,臉上寫滿疲態。他曾失去了什麼?抑或他將失去什麼?他打算趁傷感襲來前提早哀悼嗎?
我很清楚自己無意愛上另一個人。我想愛上的是更廣闊的事物,某樣能沉澱我和我漂泊心靈的事物。就如同一場戀愛,讓我能說出「我在這裡,我感覺自己活著」,而不只是靜靜地讓自己撐著。
要當一盞守夜的燈火,光是泰然自若、日以繼夜地燃燒是不夠的。
隨著我的日子被切分得越來越細碎,我發展出了糟糕的漫遊欲望。
我開始羨慕真正的漫遊者,那些在黑暗大海漂泊,或逸逃登上高山、沿著太平洋屋脊步道行走的漫遊者。我幻想自己隨著步道上的足跡走向蠻荒的所在。但我一向不是戶外型的旅人,而是都市型的,是讓城市定義自我的後殖民主義者。一想到要在日漸暖化的地球尋尋覓覓,而且對著美麗的事物驚呼,就讓我卻步。我的心理狀態也是如此。預習哀慟的感受已在我體內生根,家人生命邁入終點帶來的陰影,讓我對其他終結也充滿警戒。
死亡本身即是「有限」的定義。關於我的漫遊欲,我開始意識到,要找到那條讓我回歸無限、復返創意及沉思的心靈森林的那條路。
【十二月—愛】
當晚,我造訪了那位音樂家的網站,看見他拍攝的鳥類照片。這些照片應有盡有,而且稀奇古怪,不是那種你會在賀卡或鮮豔光燦的鳥類月曆上見到的照片。
這群鳥棲息在鋼筋、玻璃、混凝土與變電箱構築而成的家園。
有隻鳥的臉上罩著一只印著「冷凍芒果」的塑膠袋,另一隻則停在碎燈上,還有幾隻分別停在發黏的灰泥牆、鋼筋捆、大型鍛釘和鐵絲網上。這些鳥兒的行為與一般鳥兒無異:休息、飛翔、理毛、覓食、築巢──然而牠們無疑會更寧願生活在這些混亂、滿是沙泥和垃圾之外的世界。
這些照片透露的,並非平時可見的破壞環境罪行或是世界末日將至的訊息。若說這些照片真訴說著什麼,那就是愛。不是對漂亮女孩的愛,也不是對心愛之物百般呵護、擺在架上或櫥窗中的愛,更不是教人神魂顛倒、迫切渴望,甚至輾轉難眠的愛。這種愛既不理想化,目的也不在占有。我從照片中感受到的,是對缺陷與掙扎的愛,是對黯淡、樸素、美麗,或者有趣的所在──這個我們稱之為「家」的愛。
看著照片,看著鳥兒與牠們的周遭環境,我的心加速跳著。
等待世界對一件事冷靜下來時,我習慣了孤獨;身為兩名年邁移民的獨生女,我習慣了孤獨。我的父母各自離鄉背井,舉目無親來到這個嶄新大陸,在他們的人生歷史上畫出一條走向線。他們倆在這裡並不是扎根於土的樹木,反倒像是長在盆中的植栽。身為必須離群索居的作家,我習慣了孤獨。我在鳥兒的周遭看見的事物難道就是這個?我個人的孤獨?
我聯絡上這位音樂家,打算和他同行賞鳥。我想對一件事專注入迷,感覺自己仍能受到啟發。我沒將大自然視為是我私人的聖地露德,或是療癒的荒原。
又或許我有。
*
幾天後,我在街旁人行道上看見一個年輕男子正奇怪地移動著。他先是往前踏步,再往後踩,接著跨向一旁,向前踏,再踏回來。他的動作讓我想起,有時我跟先生也會裝模作樣地跳起現代舞。我好奇他為何在人行道上跳舞,於是走向對街。
躺在地上的,是隻尾巴受傷流血、飛不動的鴿子。我從袋子裡挖出一條健身房用的毛巾,將鳥兒裹起來,輕柔地將牠移到有屋簷遮蔽的門廊。我們蹲下來試著與牠交會眼神。我不曉得牠呆滯的雙眼是否看見了我們,或者牠已不在乎了。牠的動作越來越微弱,但我們持續凝視著。
我以前也見過死鳥,但未曾親眼看著鳥兒死去。理性而言,我知道這隻鴿子稱不上是什麼預兆。我不是會仰望天空、尋找神祕徵象的那種人,但近年來我開始相信機緣巧合。若非機緣與巧合讓兩個衣著隨便的人在意料之外的情況下相遇,我就不會在這裡。若非我在一個不可思議的夜裡走進一扇謎樣的大門,我也不會遇見我先生。所以在遇見這隻鴿子、而隨後幾天又不尋常地頻繁碰見鳥兒之後,我開始感覺這是老天的暗示,告訴我下一步該怎麼做。我得學習認識鳥。於是我發訊息給那位音樂家,問他之後的這一年我能否跟著他賞鳥。
音樂家說可以。
【一月—牢籠】
我很好奇,鳥兒對自己被幽禁會有何想法。牠們可會羨慕窗外自由翱翔的同伴?長期關在籠中的牠們可會渴望被放出籠外?又或者,如果牠是在鳥籠中出生,這還能稱為監禁嗎?牠們可知道自由後該何去何從?甚至雖然被監禁籠中,卻一無所知?
確實有某些故事,描述生於囚禁中的動物日後會對外界感到恐懼。雖然這似乎有違常理,但人為飼養的動物通常會意識到,牠們在野外存活的機率至多是未知數。逃走或是飛離的假想簡直太麻煩又可怕,所以牠們情願待在籠子的庇護裡。
我懂。我懂裹足不前的感受。我懂雖渴望改變、卻被困在同一個精神牢籠裡的感受。我懂在人生某個階段必須奉獻自己,努力扮演好母親和女兒、自我卻所剩無幾的感受。飛出敞開的大門變得好難,在你拚命囤積孤單、隔絕他人的同時,可能也為自己築起了高牆。
渴望自由的天性也許根深柢固,但在某些方面,你我都是囚鳥。我們可能受制於傳統,或身陷在一段越來越像籠中鳥的關係內,也許是家庭、婚姻或職業,雖然舒適且習以為常,但牢籠終究是牢籠。我們或許是畏懼於一片浩瀚無垠,或者害怕未知的墜落感而無法動彈。當我們捨棄美妙的自由而改求財富上的穩定,當日子過得像是有如廣場恐懼症般,我們於是誤以為待在上鎖的屋內才是真正的安全,這讓我們全成了囚徒。習慣的牢籠,自我的牢籠,野心的牢籠,物質主義的牢籠。免於恐懼與免於危險之間的界線,並非總能輕易分辨。
要當一隻靠著機智在野外求生存的自由飛鳥,這絕非易事。
【四月—知識】
我對鳥兒最早的記憶,是倫敦特拉法加廣場上的鴿子。我還記得當時就站在尼爾遜將軍紀念柱旁,滿手抓著麵包,被一大群飢餓、貪婪的「鴿海」包圍。那時我四歲。我記得那個留著精靈系短髮的褓母,向我示範如何把麵包屑丟出去。像這樣,她說,輕輕丟。
遷居加拿大後,我記得有種小鳥常落在學校外頭的地上。這個靜謐、綠意盎然的小地方叫「森林之丘」。那些鳥在空中飛來竄去,誤以為大片的玻璃是一條清透的通道,於是一頭撞上學校的哥德式玻璃窗。我很快就認得小鳥撞上窗戶時發出的特殊聲響,我也明白,只要小鳥和建築相撞,後者永遠是贏家。那些鳥兒就像一團團小沙袋,掉落在草地上。只要到教室外玩耍,就會在橡樹底下發現幾個煤灰色的小東西。我還記得牠們細如火柴的腳朝上指著天空。有時甚至會見到一小灘血淌流著,但小鳥只會像睡午覺似地躺著,動也不動。兩年後我離開那所學校,不曉得校方後來是否明白該為窗戶加裝窗簾,或是像其他地方那樣,在窗玻璃上貼些驅嚇鳥兒的圖案。但我記得,當時我認為小鳥只不過相信自己能飛,就得遭受如此懲罰,這實在太過殘忍。
我記得東京代代木公園的烏鴉。那年我十八歲,正跟當時的加拿大男友在公園散步。我記得烏鴉讓天空瞬間一片漆黑,記得牠們尖叫著俯衝而下,就在離我們不過幾呎外用喙嘴扯開一包垃圾。我也記得牠們寬大的羽翼揮動時發出的咻咻聲,那爪子就像卡通中巫婆的手指。我嚇到哭出來。我知道烏鴉有時會攻擊太接近鳥巢、又毫無戒心的路人。烏鴉很野蠻,會活生生啄下動物的眼珠。禿鷹至少還會等你死後才動口。
*
長大後,我每年夏天都會到東京,烏鴉每每令我膽戰心驚。那些是所謂的巨嘴鴉,看到牠們出現在整潔、無瑕的市中心裡,可說是既荒唐又可怕,那暗示著在乾淨的街道和發亮的門面背後,也可能潛伏著野蠻和失控的現實。
或許外婆家外頭還有其他鳥,但我不記得了。我只記得自己常窩在屋子裡,也還記得障子的紙是如何過濾屋外的聲音——卡車擴音器的聲音賣著烤地瓜,或是宣傳著右翼思想。我還記得滂沱大雨從簷槽順著黃銅水風鈴落下的舒心聲響。雨天是寫信給去安大略北部參加夏令營的朋友的日子;雨天也是讀書天。
在日本的漫長夏日裡,當無聊和寂寞威脅著將我生吞活剝時,我會縮進外婆家的小房間,攤開蒲團,打開電扇,然後讀書。我對書本畢生的熱愛正由此而來。
書是我最可靠的夥伴。看完家中所有的書之後,我會到新宿市區買些日本作家的小說譯本,夏目漱石、谷崎潤一郎、大江健三郎。這些書攤在榻榻米上圍成一個小窩,環繞著我,就在阿姨的佛壇旁邊,而點燃的檀木線香正飄送著一縷輕煙。
書是我的生命與麻醉劑。「書是活生生的,而且它們會向我說話。」亨利.米勒(Henry Miller)如此描述:「兒時的閱讀帶有容易被我們遺忘的重要元素——那就是某個場景的實際氛圍。這點相當明顯,多年後,一個人仍能清楚記得最愛的書帶給他的感受、印刷字體、裝訂、插圖等等。要具體說出第一次閱讀的時間、地點何其容易啊。有些書關乎自己的病痛,有些關乎壞天氣,有些關乎懲罰,有些則關乎獎勵……這樣的閱讀,無疑是人生中的一樁樁『事件』。」
我小時候是個書痴,長大後還是書痴。書為我帶來快樂,也讓我得以隔離自己,讓我在受俗世煩擾或驚嚇時,能轉身避開這世界。書讓我避開他人對我的要求、避開日常、避開家人和眼前的世界。它們在深夜給我撫慰和消遣,在我遠離家鄉時當我的友伴。
蘇珊.桑塔格在某本手記中提到,就算面對末期癌症,她也無法停止閱讀。她寫道:「我無法停止讀書……我正吸著一千支吸管。」我了解那種對文字深不見底的飢渴感,在危險時期更是如此。讀著桑塔格的文字,我想起一張著名的照片,照片上是一九四〇年倫敦遭空襲過後已然成為廢墟的某間書店。空襲警報解除後,幾個男人正神色自若地瀏覽著書架——這展現出英國人的剛毅不摧,又或許是對書的癡迷,這象徵一股傻勁,抑或壓抑不了的希望。
書本讓我珍藏了不少快樂,但我若是坦白面對自己,會知道書也從我身邊拿走了什麼。我從小說段落間窺探真實的世界;但當我應該腳踏實地時,卻又不斷追尋文字。
從那段日本時光之後,每當我翻開書頁,仍會想起榻榻米的草香。我也無法挺著身子,姿態端正地讀書。為了完全沉浸在書中世界,我一定是橫臥著。把自己用毯子像木乃伊那樣層層裹住,讀起來的效果最好。
書本有時為我帶來庇護,有時又讓我作繭自縛。
【五月—挫折】
五月,我在某個夜裡尋思「墜落」,剛好在YouTube上看見德國舞蹈家碧娜.鮑許滑稽卻哀愁的舞蹈片段「一九八〇年:碧娜.鮑許作品」。表演開始沒多久,有個女人在舞台上轉著大圈跳躍,手裡揮著白手帕。「我好——累,我好——累。」背景傳來輕快的布拉姆斯《搖籃曲》,女子也跟著有節奏地反覆說著。她不停旋轉,直到最後終於疲憊不堪,反覆的聲音開始結巴、斷續,腳步踉蹌,而賣力高舉半空、揮著手帕的手臂也隨之顫抖。
這部舞作是鮑許在長期伴侶、同時也是最親密的合作對象舞台服裝設計師博季克(Rolf Borzik)死於血癌不久後所作。
有時我們跌跤,不是因為腳下所踏的地面不平,而是因為我們不斷移動,不斷嘗試、不斷重演相同動作,一遍又一遍,最後精疲力盡。
這一刻也許強壯,下一刻卻變得脆弱。我們會跌跤是因為活著,如果幸運,就會復原。
有次,我親眼目睹一場風暴,風雨猛烈到兩棵百年老樹因而被連根拔起。翌日,我在斷枝殘葉裡走著,竟發現一些脆弱的鳥巢完好如初,毫髮無傷地落在地上。它們輕如鴻毛,卻能挺過劇烈天災。這般命運的翻轉原來就出現在你我身邊──我久久無法忘懷。我不明白這究竟代表了什麼。
——瑪麗.魯弗《瘋狂、煎熬與甜蜜:演講集》
五月,一群群候鳥過境這個城市的大樓深谷、公園和後院。某天的早餐過後,兒子和我在我們的紫丁香樹上瞧見一隻小巧玲瓏的黑紋胸林鶯。我們倆靠在陽台門邊,凝望著那隻黃色胸口帶著黑色斑紋的小鳥。我能想像牠的體重還不及一枝Sharpie麥克筆。
那隻鳥可能來自中美洲,在飛往北加拿大繁殖地的途中先在多倫多暫歇,補充能量。牠可能連續飛了六十個鐘頭,我想像牠拍振著短小的翅膀,吱吱喳喳叫著:「我好——累,我好——累」,而其他將在春季遷徙時飛越多倫多的五千萬隻鳴禽,也齊聲喊道:「我好——累,我好——累。」我們能從各式各樣的鳥兒身上學到東西,牠們也許來自遙遠的阿根廷彭巴草原和亞馬遜叢林,從逐漸消逝的南方森林家園飛往同樣瀕臨危機的北方森林。我想知道,如何才能像候鳥那樣勇敢無懼,又該如何維持那長年不衰的堅毅。
夜復一夜,一道看不見的鳴禽奔流穿越黑暗。
書籍代號:0UCR0017
商品條碼EAN:9789869516846
ISBN:9789869516846
印刷:黑白文字,附插圖四十五幅。
頁數:304
裝訂:平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