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品牌:左岸文化
出版日期:2016-03-23
產品編號:97898657273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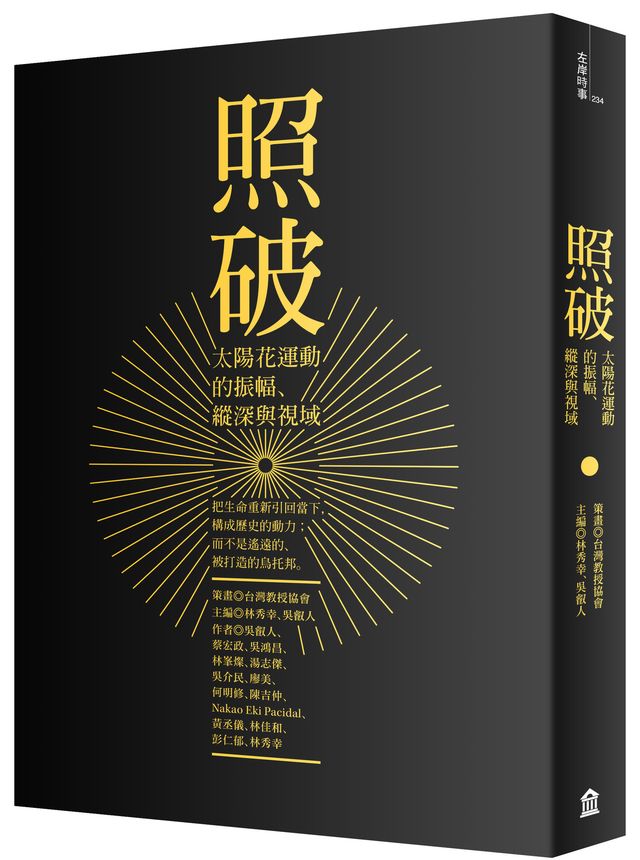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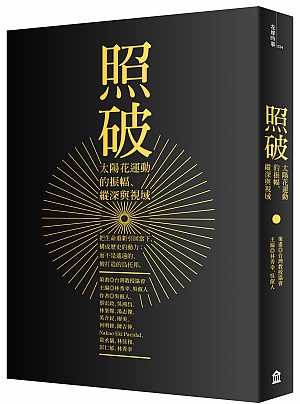
把生命重新引回當下,構成歷史的動力;而不是遙遠的、被打造的烏托邦。
2014年3月,對許多臺灣人而言,都是一次「運動」的洗禮。一場因經濟而起的爭議,卻引發了國家與社群的命題;許多人第一次經歷所謂的「街頭」、「抗爭」,第一次認真參與公共事務的辯論,第一次思考個人與國家、歷史的關係……或是,第一次認真思考,我們該如何定義自己,做為一個公民。這一次的洗禮,有人稱為「三一八運動」,有人稱為「太陽花運動」。
2016年3月,兩週年的回顧。我們該如何看待這場運動?是臺灣與中國以自由貿易為名,實則政治層面的算計角力?是臺灣公民意識/力量的勃發、社會運動的轉捩點?還是,每一個參與者生命歷程的重要分野?本書所收錄的十一篇文章,企圖從歷史脈絡、運動結構、法律和個人精神層面,來描繪「太陽花運動」所綻放出來的圖像。
吳叡人的〈黑潮論〉以「黑潮」和「帝國碎片」的撞擊為喻,鋪陳出島嶼不同階段的歷史際遇和政治塑型,以及島國內部的分化與融合。蔡宏政的〈世界體系、中國崛起與臺灣價值〉以民族國家與資產階級的互依或逆反做為觀察動線,並佐以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結構,來看臺灣今日何以落入依賴中國的路徑。吳鴻昌、林峯燦和湯志傑〈冷戰結構視野下的太陽花〉進一步邁向全球史軸線,從冷戰和後冷戰的脈絡,聚焦臺灣、美國和中國之間的關係,以及這組關係如何成為激發太陽花最直接的力道。
歷史脈絡之後是運動剖析,社會科學的理論對在地者有什麼意義?吳介民和廖美在〈占領,打破命定論〉結合理論及數據,披露社會大眾關心的中國因素是什麼?哪些人支持太陽花運動?最近幾年臺灣民意發生了什麼變化?以及,太陽花運動導致了哪些政治影響?何明修的〈政治機會、威脅與太陽花運動〉以蒂利的政體模型,從機會和威脅的角度分析太陽花運動過程的政治脈絡、歷史情境和「人際」互動,並對理論模型加以修正,呈現「人」為何是社會運動的關鍵。陳吉仲〈太陽花運動的經濟論證〉透過經濟學方法的抽絲剝繭,分析兩岸服貿的特殊性,以及究竟該如何評估自由貿易利弊,最終的提問是:什麼才是經濟的根基?自由貿易、人民幸福,何者才是目的?
Nakao Eki Pacidal的特別邀稿〈投幣式卡拉OK──部落點唱「湯蘭花」〉從原住民的位置看太陽花,除了內容,文章本身也從「形式」的自我「越線」,體現「動能」的持續,充分反映這是一場反抗和展現生命力的運動。
兩位法律學者分別從法律的不同面向切入。三一八是一個憲政危機的防禦行動嗎?黃丞儀在〈未完成的革命〉中告訴我們,這個問題不僅是法學、也是政治哲學的議題,身處一個具有「例外狀態」和「民主困局」的特殊憲政格局,如何既要反叛、又要依脈絡而行,將考驗我們對「民主」和「共和」承諾的意志。「將政治問題法律化,政治將所獲無幾,而法律全盤皆輸。」林佳和〈一場重新定義法律的運動〉以施密特的名言起頭,「三一八學運,合法或違法?」貫穿提問,這批運動者實則在不同具體關聯上,於前後相異的階段中,面對法律,定義法律,重新找回或創造自己要的法律內涵。
第一次,臺灣有學者以精神分析理論談論一場劃分歷史的社會運動。彭仁郁〈反叛中建構的主體〉從拉岡和克里斯蒂娃提供的視野,讓讀者領略一場由「反叛」所發動的「主體化」過程,不只停留在表層的政治倫理,而是直入微細的「野蠻驅力」、「欲望」和「認同」的深層心理世界和社會集體史的交錯。最末,林秀幸〈太陽花的美學與政治實踐〉企圖以社會詩意和空間詩學來看太陽花的政治伏流。一個從空間現象學辯證而來的政治解讀,如何讓維護親近性空間成為正當性的美學行動?這樣的動能又能如何推擠出臺灣獨立的政治地景和歷史方向?
這十一篇文章,不約而同地,把研究視野拉回具有創造性的人。不再強調定義分明的概念,把「生命」放回歷史、把「生命」放回研究視野,讓人的生命重新主導政治,讓人回到歷史場景,構成歷史的動力,幫助我們拉開觀看社會運動更豐富的角度。
吳叡人(中研院臺史所副研究員)
蔡宏政(中山大學社會系教授)
吳鴻昌(中研院社會所博士後研究員)
林峯燦(中研院社會所博士後研究員、東海大學通識中心兼任助理教授)
湯志傑(中研院社會所副研究員)
吳介民(中研院社會所副研究員)
廖 美(中研院社會所博士後研究員)
何明修(臺灣大學社會系教授)
陳吉仲(中興大學應用經濟系特聘教授)
Nakao Eki Pacidal(馬太攻守聯盟)
黃丞儀(中研院法律所副研究員)
林佳和(政治大學法律系副教授)
彭仁郁(中研院民族所助研究員)
林秀幸(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人文社會學系副教授)
占領,打破命定論(摘錄)
吳介民(中研院社會所副研究員)、廖美(中研院社會所博士後研究員)
四、占領行動的主體與創意
前節闡述太陽花運動發生的因素、以及反服貿運動的歷史脈絡。這場占領,不但震撼臺灣政局,創造一種新形態的抗爭政治,也讓臺灣的抗爭聲音傳播到世界,並讓美中兩國都做出回應。這節將說明運動參與的主體、過程及其效應。
(一)學運力量、青年世代、公民社運組織的匯聚
太陽花運動的參與主體是誰?很明顯的,學生與青年的角色至關緊要。三月十八日衝進立法院的主力是學生與青年。因此,不少人把這個運動稱為「太陽花學運」。但是,我們也不能忽略,這場運動中,公民組織與社運團體所扮演的角色。把時間的視野拉長,學生、公民社運組織、長期參與民主運動的先行世代,都是這波運動的參與主體。
回答「太陽花運動的參與主體是誰?」這個問題,同時涉及這場集體行動的空間性質。由於在立法院議場內的占領者(以學生為多數),被警察包圍;抗爭者要進出議場內外時,必須通過警察的封鎖圈,也必須通過占領者的糾察線。因此,抗爭空間便呈現三層結構:最內圈(第一層)是占領者、中間是警察、外圍是支援的抗爭者。議場內外的抗爭者之間的溝通協調型態,便呈現多元行動中心。當然,議場內外的抗爭者每天進行「聯席會議」,但是許多行動決策並非通過這個聯席會議做出決定。議場內有比較具有向心性的核心「決策小組」(九人小組),但議場二樓仍然存在一群守衛者的「奴工」,有獨特的自我認同。而在立法院四周所形成的對議場占領者的「保護層」(第三層),參與者的成分與背景則高度多元而複雜:有來自各種公民社運團體,其成員不乏各類社運幹部、人權組織、環保組織、工運組織、媒體改革組織等等,以及教師與積極公民。這些人當中,許多在過去幾十年民主化運動過程都曾是積極分子,例如傳統臺獨運動世代、一九八○年代的「野百合運動世代」、一九九○年代「社運黃金年代」的幹部、二○○○年代的「反樂生療養院迫遷運動」的參與者、以及二○○八年的「野草莓運動世代」;加上許多難以使用「既定語彙」給予稱謂的參與者,比如自發在立法院周邊擔任糾察工作、但在組織上不屬於「糾察隊」的計程車司機與「兄弟們」,以及許許多多「沒有臉孔的人」。
這些NGO組織幹部與參與者,在立法院四周舉辦了各式各樣活動,並且展開各種組訓培力,如「非暴力抗爭訓練」、「公民審服貿」(D-Street)與「人民議會」(嘗試將審議民主、公民會議的溝通模式,轉到街頭活動上)、「開放論壇」(讓圍觀者成為發言主角)、「街頭公民教室」等等。此外,還有「賤民解放區」、「大腸花」等與運動主流旨趣不同的論壇。多元而異質的抗爭模式不斷翻出,是太陽花運動可以延續二十四天而不致「冷場」的關鍵因素。從另一個角度,占領行動適時接隼了公民社會與社運場域的各種聲音,將之轉化為自發的社會行動。其中,社群媒體(social media)如臉書扮演多大程度的動員?一項在運動現場針對參與者的大規模訪談,反駁了多數參與者是被「網路動員」說法;相反地,他們傾向自身的參與是「自發性」的行動。
(二)自發與創意
除了自發參與,這場運動的有序分工,也值得注目。當時,只要到立法院內外走一趟,即可發現一個令人好奇的問題:數以千計的參與者,聚集在臺北市內一個街區,日夜在一起工作、生活、進行抗爭,如何不產生嚴重的公共安全、衛生或其他問題?
學生與公民團體提供了各種後勤援助,使這個「無政府」的有序空間得以成立,包括飲食(飲水、便當、點心、「戰地廚房」)、臨時廁所與淋浴設施、舞台音響設備、帳篷、睡袋、垃圾分類、網路設施、醫療團隊、法律顧問、甚至心理諮商服務。而在運動本體的組織分工上,我們可以觀察到數以百計的學生與青年投入這些工作:現場主持與指揮、媒體聯絡、多國語言翻譯、文稿撰寫、糾察與安全、決策團隊、聯席會議等等,組合成一個「臨時擬政府」。此外,社群媒體和虛擬空間也提供抗爭活動的載體,許多網路社群更即時提供各式各樣的服務與訊息。當然,在這樣的抗議運動場合,還有無數充滿創意的海報、塗鴉、與藝術作品。至於無序或有序,只是相對概念。議場內以及議場內外之間的溝通不良、信任等問題確實存在,各種人際與團體間的矛盾也經常可見。其中,原運分子離開在青島東路和濟南路的「主場」,轉到捷運善導寺站三號出口附近的一個公園另闢戰地聚講(參見本書Nakao Eki Pacidal的文章)。但總體而言,這場運動仍然展現出高度的自治能力。可以這麼說,自發與自治是這場運動最成功的標誌之一。「無政府空間」與「臨時擬政府」並立,構成有趣的對比與張力,值得未來更深入探究。
充滿義憤、活力、與創意的青年學生,是運動的主力。青年世代對中國與兩岸關係的一般態度,以及對自由貿易的不滿態度正在醞釀中。二十年來,臺灣處在「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衝擊下,已經產生許多社會問題,包括貧富差距擴大、青年失業率上升、勞動貧窮人口增多等等。青年世代被稱為「崩世代」或「22K世代」(每個月賺取兩萬兩千元臺幣的薪資)。太陽花運動的年輕參與者除了大學生與高中生,還有不少剛進職場的青年,其中女性也占了大半。青年學生強烈感到「被偷走的未來」,或者前途茫茫,終於在這場運動中,找到抒發不滿的門路。在示威中,一條橫幅寫著:「拒絕去中國當台勞,待業青年接力反服貿」。而塗寫在立法院大樓外牆上的「當獨裁成為事實,革命就是義務」,更直接傳達青年的憤怒。「大腸花論壇」則提供另類的發言空間,參與者透過粗口開罵,顛覆統治秩序(演說者必須以「幹××」做為發語詞),直接對「國民黨」、「馬英九」和「中國」罵幹。尤其令人讚歎的是,參與大腸花的演說者不乏充滿創意而憤怒的女性聲音。在大腸花論壇裡,百無禁忌的「罵幹論述」(curse discourse),也是一種「論述狂歡」(discursive Mardi Gras)的縮影,它呈現臺灣青年世代的認同變遷,相對前一輩人,年輕人更能自在地表現認同。
就本文關心的軸線─臺灣公民社會如何抵抗中國因素─青年世代的「論述狂歡」所揭示的臺灣認同強度是驚人的。他們無畏於說出、也不吝於說出「我支持臺獨」。在這樣的言說互動中,解構「臺獨的污名」,也抵抗中國政府對臺灣獨立支持者的恫嚇。換言之,這場運動是「價值宣誓,宣誓『我們沒有被說服,被中國的大國價值所說服』」。
對於中國政府而言,原先「統戰策略」設想的是,培育一群親北京的財團與政客、收買媒體引導輿論,便可以「解決」臺灣人的認同問題。但是這個「認識框架」已經被太陽花運動無處不在的「論述狂歡」所顛覆。對年輕世代而言,臺灣人認同屬於集體靈魂的尋索過程,是在日常生活的細微互動中點滴累積起來,其紮實、頑抗性遠高於「中國中心主義者」所能想像。
換言之,北京「收買臺灣」的策略,現在反而變成一個難題。而北京似乎也很快在調適這個新現象,試圖做出回應,聲稱將「聽取臺灣年輕人的意見」。
五、誰支持太陽花運動?
前兩節描述太陽花運動積極參與者的理由、主體、過程及其效應。那麼,在社會層面,哪些人支持太陽花運動?支持或反對的變數是什麼?根據中國效應研究小組(CIS)在二○一五年進行的問卷調查,我們使用二元邏輯回歸(將贊成太陽花運動歸碼=1,不贊成=0),檢證幾組變項後發現,民眾是否支持太陽花運動,主要的顯著變數包括:政黨因素、中國因素、對民主與政府的評價、世代/年齡、教育、統獨選擇、以及婚姻狀態。
在政黨因素方面,不同的政黨認同讓民眾表現出支持態度的差異:偏綠的政黨認同傾向支持太陽花,而偏藍的政黨認同則傾向不支持。認為國民黨政府太過「傾中」的人,強烈支持太陽花運動,這個變項的影響力是所有變項中最高的;在分析樣本中,有百分之六十四的受訪者認為國民黨政府太傾中。此外,比較信任民進黨政府與中國進行談判的,也明顯支持太陽花運動;在分析樣本中,信任民進黨政府進行談判的人有百分之四十六,而支持國民黨政府的只有百分之三十九。同一個問題,在二○一三年調查時,民眾對國民黨的信任高於民進黨,當時信任國民黨政府代表談判的有百分之四十九,信任民進黨為百分之三十四。很明顯,民眾的態度在二○一四年太陽花運動之後,發生了翻轉。
中國因素方面,在目前兩岸關係下擔心失業者傾向支持太陽花。關於兩岸交流協商中,認為國家主權比經濟利益重要的人傾向支持太陽花。此外,認為中國未來可能民主化的人,也傾向支持太陽花。但認為中國將持續快速經濟成長的人傾向反對太陽花。這組結果呈現,民眾對中國因素的考量乃是基於自身經濟利益的評估,並且在總體層面衡量經濟利益與國家主權孰輕孰重。顯示民眾的態度並非情緒性的所謂「逢中必反」,而是理性計算,尤其民眾的考慮中,還包括對中國民主化可能性的評估。
在統獨方面,傾向獨立的民眾,相對於中間態度者,比較支持太陽花運動,而偏向統一的民眾則不支持。但就實質影響力而言,統獨因素的重要性低於政黨因素、中國因素、與世代因素。綜合中國因素與統獨選擇,我們發現臺灣的國家認同議題存在一個浮現中的「生計概念」,與我們之前一篇論文針對二○一二年總統選舉投票行為的分析一致,亦即,當考慮了中國因素,原先統獨選擇對行為或態度的影響降低了,臺灣國家認同的內涵,可能正在經歷著巨大的變遷。
教育因素的分析顯示,相對於國中以下教育程度者,高中職與專科學校的畢業生呈顯反對太陽花;但是大學以上教育者(一樣相對於國中以下教育背景)則不顯著。婚姻狀態方面,已婚狀態者比較反對太陽花。
民主評價與政府評價方面,認為民主制度好於獨裁制度的人傾向支持太陽花。對政府評價(即評判當政的馬政府)好的人則反對太陽花。
世代/年齡方面,年輕人顯著支持太陽花。十八到二十四歲對比於三十五到四十九歲,支持太陽花的機率是二點七倍;二十五到三十四歲年齡層,相比於三十五到四十九歲年齡層,則是一點六倍;反觀六十五歲以上老年人則傾向反對太陽花運動。這個發現證實了年輕世代對臺灣政治事務的關心程度正在提高,而且也跟晚近「年輕世代臺獨化」的命題吻合。觀察民眾的統獨選擇:不分年齡,選擇統一有百分之十六,選擇獨立有百分之四十六,中間立場為百分之三十八。分不同年齡層觀察,特別在十八到二十四歲年齡層,只有百分之二選擇統一,他們有高達百分之五十九選擇獨立,另有百分之三十九選擇中間立場。要言之,愈年輕,選擇獨立的比例愈高(圖一)。
總體而言,對太陽花運動的支持與否,政黨因素的實質作用力最大,中國因素次之,再來依序為世代/年齡、對民主與政府的評價、教育程度、統獨選擇、婚姻狀態。這裡需要注意的是,在分析歸類為政黨因素的變項,其實也包含一定程度的中國因素成分,例如國民黨政府是否過度傾中、兩岸談判比較信任哪個政黨等題目,就涵蓋了臺灣與中國關係的評估;換言之,這幾個變項測量已「被中國因素化」的政黨因素。
最後,我們需要討論那些在直觀上重要、但在統計上不顯著的變項。首先,階級變項全部不顯著,省籍、所得也都不顯著。至於,本文關切的「人們對於自由貿易的態度」呢?統計結果顯示,受訪者中有百分之七十三贊成與中國擴大自由貿易,反對者有百分之二十七;百分之九十贊成與美國擴大自由貿易,反對者只有百分之十。臺灣的一般民意幾乎一面倒支持自由貿易。但是,不論是「跟中國大陸擴大自由貿易」或是「跟美國擴大自由貿易」,贊成或反對的立場,都與支持太陽花與否在統計上沒有顯著關聯。
以上發現,指出兩個特點:第一,太陽花支持者與太陽花運動幹部/積極參與者之間,存在著關注議題的差異。太陽花運動積極參與者中,有一部分人反對服務貿易的理由是反對自由貿易,這個現象可以由抗爭現場的海報布條與論述獲得證實,儘管我們無法確定其比例程度。但是,一般民眾支持或反對太陽花與他們對自由貿易的態度無關。第二,晚近青年政治運動蓬勃發展,被認為是左翼民族主義正在興起,或者民族主義社會的基礎向左移動。但是,在一般民眾層次,調查資料顯示階級因素並不顯著。
六、「被統一」的焦慮與張力
太陽花運動的爆發,民眾對此集體行動的支持與否的態度,以及此行動對民意的影響,都與臺灣人民的政治認同息息相關。而且,近年來,民意對中國相關因素的態度,顯示出民眾對中國影響力的認知在升高。在臺灣政治深層,一個主要的伏流是「被統一」,或是臺灣被中國兼併的焦慮。我們先從國族認同的變化趨勢談起。
臺灣人認同的持續上升
根據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TEDS)長達二十餘年的調查,從一九九四年以來,臺灣人認同一直呈現穩定增加的趨勢(圖二)。臺灣人認同在一九九四年占百分之二十,低於中國人認同的百分之二十六。但是到了二○一五年,臺灣人認同已高達百分之五十九,而中國人認同則只有百分之三點三。雙重認同(是臺灣人也是中國人)在一九九四年是百分之四十五,到二○一三年則為百分之三十四,呈緩慢降低。從圖中,可觀察到臺灣人認同與其他兩種認同的交叉。第一,在一九九五年,臺灣人認同超過中國人認同,此後持續拉開差距。第二,臺灣人認同在二○○八年超過雙重認同,此後也拉開差距。值得注意的是,在二○○一~二○○七年之間,大約是陳水扁執政階段,臺灣人認同與雙重認同處於拔河狀態;臺灣人認同在馬英九執政階段大幅度領先。因此,可以得到一個暫時結論:在馬政府執政期間,其拉近與中國關係的大陸政策,加上中國因素開始在臺灣發生作用,在民意態度上,反而伴隨更為高漲的臺灣人認同。
年輕人臺獨支持率上升
年輕世代對臺獨的支持度,近年來也呈現增加趨勢(圖三)。二○一一年,青年世代(二十到三十四歲)中支持臺獨者有百分之四十三,與平均值相當;壯年世代(三十五到四十九歲)為百分之四十二;中老年人(五十歲以上)則是高於平均值的百分之四十五。到了二○一二年,情況有點改變,青年世代臺獨支持率升高到百分之四十六,高於平均值;對比之下,壯年世代是低於平均值的百分之三十九,比前一年低百分之三;而中老年人則是百分之四十四,也比前一年低,但仍高於平均值。二○一三年,青年世代的臺獨支持率增為百分之四十九;壯年世代為百分之四十二,比前一年稍高;中老年人則降至百分之四十三,低於平均值。二○一五年,經過太陽花運動與九合一選舉,青年世代的臺獨支持率大幅上升,增至百分之五十六,比平均值高了百分之十;壯年世代也提升為百分之四十六;但中老年人則持續降低到百分之四十一。從這四年間的調查數字,可清晰看到幾個變化。第一,臺獨支持率總體而言有升高態勢,但速度相對緩慢。第二,壯年世代的百分比與總體分布很接近。第三,中老年人則呈相反方向變化,對臺獨的支持率連年降低。第四,青年世代對臺獨的支持度,逐年上升,以二○一三到二○一五年的攀升最為顯著。支持臺獨不再以中老年人為主力,而是年輕人的新潮現象。
對中國影響力的認知
接著,觀察臺灣民眾對中國政府影響新聞媒體的評估。圖四呈現CIS二○一三年的調查,全體受訪者有百分之七十一同意「中國大陸政府對臺灣媒體的政治立場影響越來越大」。其中,在十九到二十四歲和二十五到三十四歲兩個年齡層,都有百分之七十九同意這個看法,高於中、老年齡層。整體而言,同意的比例隨著年齡層的降低而遞增;不同意則隨著年齡層的降低而遞減。
被統一的焦慮感
統獨爭議連綿數個世代,攸關國家前途的預期落差,可能造成巨大的政治結果。以往對於統獨態度的調查研究,只針對受訪者當下的選擇做調查,並不觀察受訪者對時間向度的敏感性。CIS二○一五年的問卷調查,增加了一個題目:「請問您覺得未來兩岸關係最有可能出現什麼結果?」答案選項包括:「臺灣被中國大陸統一」、「臺灣獨立」、「維持現狀」(圖五)。我們把這一題的測量結果,與當下統獨選擇做對照,發現在「當下統獨選擇」與「預期未來兩岸關係」之間,存在著明顯落差。在當下統獨選擇的維度,多年來,「統一」支持者逐漸萎縮,二○一五年調查只有百分之十六受訪者選擇統一;但是,當詢問人們對未來趨勢的評估,卻有高達百分之五十預期「臺灣被中國大陸統一」,落差高達百分之三十四。「獨立」已成為當下選擇的主要選項,有百分之四十六;但評估將來可能獨立者則為百分之三十六,落差達到百分之十。當下選擇「中間立場」的人有百分之三十八;然而,預估臺灣未來可以繼續「維持現狀」的人,只有百分之十四,落差為百分之二十四。這樣的預期落差,一方面可能造成社會焦慮,一方面也可能產生政治張力。
統獨與太陽花支持率
我們進一步探究,關於統獨的預期落差,會不會表現在對太陽花運動支持率的差異?當下統獨選擇與預估兩岸未來這兩個變項,各有三個選項,可以構成「九種」態度,由於以選擇統一與三種未來走向預估交叉分析後,次樣本太小,在此省略這部分的分析。最後,我們將「六種」態度與是否支持太陽花運動進一步交叉分析,發現:(一)凡是當下選擇獨立者,不論預估未來是何種結果,對太陽花的支持率都超過平均支持率的百分之五十:預估被統一者為百分之六十五,預估獨立者為百分之六十九,預估維持現狀者為百分之六十七,三者間差異不大。(二)當下選擇為中間立場者,其對未來結果的評估不同的人,對太陽花運動的支持度呈現顯著差異:預估被統一者有百分之四十支持太陽花,預估獨立者為百分之五十一,預估維持現狀者為百分之二十八。(圖六)
選擇獨立者支持太陽花運動不難理解。但是,「中間立場,預估被統一者」,同時支持太陽花運動的比率有四成,雖然低於總體分析樣本的平均支持率,但仍顯著高於「中間立場預估維持現狀者」。這個統計關聯性如何解釋?以我們目前的研究資料,尚無法提出決定性的解答。不過,如果把調查發現放到政治情境中檢證,則可以提出一種詮釋:人們因為擔心臺灣的「現狀」維持不住,而選擇支持太陽花,甚至直接參與占領行動。換言之,拒絕統一的人(不論是選擇獨立或中間立場),因為擔憂「被統一」,而在國家遭逢政治危機時,願意採取行動,抵抗「被統一」的趨勢。這個心理機制,雖然不能解釋所有支持或參與太陽花的人,但至少能夠解釋一部分人的心理狀態,他們並沒有坐困於理想與現實的鴻溝,聽天由命,而願意挺身而出。
綜合而論,關於臺灣民意對中國因素相關的態度變化,可以得到以下總體圖像:
(一)政黨因素(包括中國因素化的政黨因素)、中國因素、統獨選擇,是支持太陽花運動的關鍵變項。
(二)近年來,年輕人支持臺獨比率升高,以及年輕人對太陽花運動的高度支持,可能凸顯一個現象:一個以臺灣認同為根底的青年政治世代正在興起之中。
(三)儘管選擇統一者是少數,但是臺灣社會瀰漫的「被統一」的焦慮感,可能在重要的政治時刻產生很大的政治張力,並激發集體行動。
以上兩節以量化資料呈現太陽花支持者面貌以及近年來快速變動的政治認同。但需注意,太陽花運動中的青年文化,也展現了認同政治難以量化的一面,例如前述「罵幹論述」的豐富內涵。計量研究累積不少對臺灣認同議題的認識,但這些知識的積累主要放在相對靜態的「模型」與「框架」中詮釋。這類知識有其必要,但認同政治不只是「調查資料」與「統計數據」的算數而已。雖然從調查中,我們獲知青年世代關於國族認同與其他議題態度的比例,但「數字」中人們認同內容的動態與複雜度,需要更多深度訪談來補充。
未完成的革命:三一八運動迎接的公民共和曙光(摘錄)
黃丞儀(中研院法律所副研究員)
“We are discussing no trivial subject, but how a man should live.”
─ Plato, Republic, 352D
三一八運動在二○一四年四月十日結束占領立法院,宣告落幕。長達二十四天的占領期間,發生許多波瀾壯闊的事件,持續重擊臺灣社會的心臟。從退場以來,不斷有各種討論,去分析、思考這場規模龐大的社會運動究竟對臺灣的民主政治產生了什麼意義?尤其隨著香港在同年九月底開展「和平占中」的雨傘運動,乃至於隔年七月日本社會因為首相安倍晉三力推安保法案,試圖不經修憲程序而解除憲法第九條對於使用武力的限制,造成民間社會大幅反彈,甚至引發戰後最大規模的示威遊行。一時間東亞社會瀰漫著一股「對抗國家權力」的大革命氣息。三一八做為濫觴,究竟只是一場反對區域自由貿易的社會運動,還是對馬英九政府不信任的政治表態,抑或是反中、支持臺獨的情緒發酵?坦白說,在事件發生二週年後,還未必說得清楚。英國政治哲學家柏克(Edmund Burke)曾在《法國大革命反思》中寫道:「當我看到自由的精神付諸行動時,可以看見背後有種強烈的原則在支配;而這就僅是我暫時所能知道的一切。當不穩定的氣體直接釋放時,我們得先停止我們的判斷,直到最初的激盪沉澱下來,直到激情揮發掉,直到可以看到某種要比表面混濁的泡沫動盪更深一層的東西。」或許我們應該將三一八放到一個更長的歷史視野中,才能清楚掌握占領行動背後的深層意義。
眾多論者都認為三一八運動發軔於馬英九政府打算強勢通過服貿協議,製造了所謂的「憲政危機」,或者至少產生了「憲政危機」的可能性。因此,占領立法院就是為了防禦此一「憲政危機」,而不得不採取的行動,占領者進而可以主張「公民不服從」或是抵抗權的行使。關於馬政府強推服貿的作為是否製造了「憲政危機」,有不同的法律見解,需要更細膩地討論。不過,幾個前提問題就足以讓人產生許多困惑,比如說:「憲政危機」的定義是什麼?由誰來認定?即便出現「憲政危機」,是不是可以直接上綱到「公民不服從」的層次進行抵抗?如果在法院主張公民不服從,終究是由法院來進行判斷,公民可不可以不服從法院對於「公民不服從」的判斷?本文認為,三一八運動最重要的意義並非單純防禦「憲政危機」,而是透過公民積極參與,展現出了一股「憲法創生」的欲望。這股「求生存」的欲望,與其說是帶來了「憲法時刻」,不如說是「公民共和」(vivere civile)昂揚的時刻。當公民熱心參與政治社群的公共事務,懷抱公共福祉去討論和行動時,一股上升的共和意志於焉生成,帶來「重新塑造憲法權威」的政治動力。然而,這股「公民創生」的共和意志在現實上遭遇到艱困的政治障礙,以至於即便五十萬人上街頭,也未能創造新的憲法權威(constitutional authority),憲法時刻消散如雲煙。但是,三一八運動的矛盾點也在於此,《中華民國憲法》本文對於當前政治社群的公民屬性(citizenship),造成了制度性障礙。我們可以說,三一八運動其實是臺灣做為一個政治社群,意欲重新進行自己表述(self-representation,或自我代表)的大規模公民運動。只是,自我表述的意欲雖然強大地呈現在占領立法院的行動中,卻仍無法改變目前《中華民國憲法》的憲法權威,導致這項「自我表述」欠缺規範效力,未能完成它所期待成就的任務。
解嚴之後,臺灣也曾經歷過一次重新進行自我表述的歷史機遇。一九九一年,受到前一年野百合運動的推促,時任總統兼國民黨主席的李登輝主導政治改革,廢除了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並由尚未改選的第一屆國民大會代表(俗稱老國代,或「萬年國會」)通過〈增修條文〉。〈增修條文〉的前言明白指出其制定目的是「為因應國家統一前之需要」,因此將當時仍同屬「國會」的三個機關:國民大會、立法院、監察院,選舉範圍限縮在「自由地區」;而中華人民共和國則名以「大陸地區」。第一次〈增修條文〉的自我表述,是在黨國機器操作下產生的政治妥協,與三一八運動的性質與過程大不相同。然而,直到最近一次修憲(二○○五年),仍舊維持著第一次〈增修條文〉所創造的自我表述。換言之,從憲法政治的層次來看,臺灣這個政治社群在過去二十四年始終重複宣稱同一種政治身分。即便修憲七次,國民大會已經消失,監察院也失去了國會的地位,總統從間接選舉改成全民直選,行政院院長由總統任命不需立法院同意,〈增修條文〉中「國家統一」的前提和第十條蘊含的「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為共同政治社群,始終未受改變。換言之,直到三一八運動引發既廣且深的「公民共和」時刻,臺灣這個政治社群幾乎沒有大規模、全面地檢討過自身的公民社群認定。
三一八運動的參與者在運動過程中,逐漸認知到《中華民國憲法》在政治社群定位上產生的矛盾。因此,所謂「天然獨」的年輕世代衝決而出,試圖重新界定臺灣政治社群的構成(political constituency of Taiwan)。這種尋找政治社群重新定義的生命能量,不必然以修憲的形式來自我完成。從事後觀點來看,三一八運動提出的「公民憲政會議」要不被扭曲為「經貿國是會議」,要不就被窄化為「總統制或內閣制」的中央政府體制調整議題。如此修憲反而重蹈過去二十四年七次修憲的覆轍,企圖以由上而下的政治妥協方案來進行制度改造,不可能提高政治社群的公民積極動能(active citizenship),擴大民主程序的包容性(inclusiveness
),凝聚新的共和意志,創造出憲法權威所需的政治基礎。三一八之後,常態民主的縣市長、國會、總統定期改選反而沖消了「公民共和」時刻的高昂政治動力,將所謂深沉的民主(deep democracy)所需的公共審議和公民參與,消弭於政治過程之外。以「常態民主」來淡化、消除「深層民主」的需求,造成民主價值的衰貶(deflation of democratic value),也是一九九○年代「寧靜革命」(中華民國在地化)所預支的「待償貸款」,其結果深深影響臺灣人民對於憲法權威的認知。這將是臺灣未來在憲政共和發展上最需要克服的制度性障礙。
一、「服貿爭議」中正當性危機的雙重螺旋結構
讓我們再次回到三一八運動的引爆點:服貿協議的三十秒通過,究竟蘊藏了什麼問題?
眾所週知,服務貿易協議是《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的一環,也是全球各地正在不斷形成的各種區域貿易協定之一(其他類似的區域貿易協定如《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議》,TPP)。這種發展是後冷戰時期國際社會不斷交流下的政治經濟產物,臺灣做為高度依賴貿易進出口的國家,在區域整合日益密切的狀態下,自難置身於這股潮流之外。但是,一般貿易自由化協定的締結主體是區域內的主權國家,ECFA卻是在所謂「兩岸」的架構下,由臺灣的民間團體海基會和中國的白手套機關海協會,共同締結而成。此一作法自從一九九二年通過《兩岸人民關係條例》以來,歷經二十餘年,已經成為兩岸事務性協商的基本架構。尤其,一九九一年第一次修憲就已授權立法院制定《臺灣地區和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通稱《兩岸人民關係條例》),其中第四條之二授權由陸委會,委託民間團體(亦即海基會)進行兩岸事務的協商談判和協議簽署。
既然這套作法行之有年,也有憲法和法律位階的授權基礎,何以在服貿協議觸礁?服貿協議的爭議可以分為兩個層次。在第一個層次,它屬於高度技術性的國際貿易規範,蘊含了大量的政策知識和專業判斷,通常只要經過國會的事前授權或事後認可,在民主程序上就沒有太多可議之處。除非有程序瑕疵,否則司法也很難介入。人民頂多只能透過下一次選舉來表達反對意見,進而改變政治進程(political agenda)。在這個層次,著眼點是如何控制行政部門的政策選擇以及技術官僚的談判內容。但在第二個層次,服貿協議牽涉到的並非一般國對國的貿易談判問題,而是臺灣和中國之間曖昧不清的政治定位。服貿協議不是在世界貿易組織(WTO)的框架下進行,而是在特殊的「一個中國」原則下進行的談判。而「一個中國」原則是否為臺灣當下的政治社群所接受,就不是單純技術官僚可以處理的問題,也不會是形式性的國會保留原則(國會以法律授權行政部門締結技術性規範)能夠解決的問題。
當代民主國家經常將第一層次的決策權力,透過憲法所創設的權力機制予以正當化(legitimation),藉以吸納決策過程中的異議,維持政治社會的穩定。尤其在二十世紀後半葉,為了因應利益團體政治、經濟不平等、科技高度複雜化、風險社會出現,因此大量使用所謂「法治國」原則來切割責任政治的範疇,假設國會裡面的立法者保有最終控制權;但在一般行政決策的層級,可以透過法律授權,一方面滿足合法性的需求,另一方面避免行政濫權,造成民主崩潰。而這種偏向形式控制的解決機制,同時也意謂著只要在國會取得多數席次,行政部門就可以獲得授權,政府決策也就取得了合法性基礎。就臺灣的情形而言,這種決策權力正當化的過程,一方面在規範面賦予行政機關進行兩岸經濟協商的授權基礎(如《兩岸人民關係條例》),另一方面也在制度上增加立法部門進行事後控制的空間(如比照《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的行政命令審查程序)。但是,若將臺灣憲政體制上行政立法的關係納入考察,此一決策權力正當化的機制就會比我們想像的更為複雜。
基本上,採行這種國會可以事前授權、事後審查機制的,多為議會民主制的國家,畢竟行政部門的權力完全來自於國會,自應受到國會控制。然而,在總統掌握行政權的國家,國會和行政部門各自享有獨立的民主正當性來源,對外貿易事務是兩個政治部門分享權力、互相協力,而非單純由國會來控制行政部門。因此,在議會民主制國家,決策權力正當化的條件相對單純,由國會做為發動與控制的權力主體;但在總統制國家,必須透過總統、國會和行政部門之間的往復溝通與審議,以民主競爭的方式來予以正當化。
臺灣因為受到修憲的影響,比較難確認決策權力正當化機制的運作方式。《中華民國憲法》本文沿襲議會民主制的精神,要求行政院必須對立法院負責,總統僅屬國家元首,與行政權運作沒有必然關聯。但是,九七修憲後,行政院院長直接由總統任命,不再需要立法院同意;加上總統直選,中央政府體制往「總統制」(或「半總統制」)的方向移動,亦即總統可以透過任命行政院院長間接控制行政部門,行政院院長成為總統和國會中間的樞紐,總統不直接面對國會,國會也無從干預、分享或促進總統的權力行使過程。在這種狀況下,究竟何種決策權力正當化機制才符合憲法要求,遂成一大問題。
如果是側重「權力融合」的議會民主制國家,就應該偏向「國會至上」原則,以立法權來控制行政決策。(大法官在解嚴前後開始引進德國的「依法行政原則」,便是此例。)如果是像權力分立的總統制國家,就應該透過權力間的制衡對抗、審議溝通,達到政策正當化的結果。(我國大法官在第六二七號解釋中僅承認總統在特定領域為最高行政首長,行政院院長在一般意義上仍為最高行政首長。但總統和國會的關係並無明確規範。)我國既非純粹內閣制,亦非完整的總統制,雖說是半總統制,但此種說法也有爭議。所以,在臺灣的公法學討論中,行政行為的合法性控制經常只停留在法律保留原則的討論,有關政治課責的正當性基礎往往直接跳躍到選舉結果,而非藉由憲法上權力分立機制來證成。民主選舉、權力分立和合法性控制,在此被切割成不相關的概念。
兩岸協議的狀況,行政機關僅依《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第五條對於協議審查的形式分類(是否涉及「法律保留」),來決定該協議是否需要送交立法院進行審查。從形式上來看,雖未違反以國會為核心的決策控制模式,實際上卻徹底忽略總統掌控行政權時,應該盡可能採取往復溝通與實質審議的方式,以將其決策正當化。即便獲得選舉賦予他的權能(mandate),但他仍需受到權力分立原則的拘束。服貿協議的病灶就是在決策權力正當化機制不明確的狀況下,徒以法律保留原則來進行控制,造成憲法應該發揮的權力分立機制完全沒辦法實質正當化決策權力。
服貿爭議中第一個層次的「決策權力正當化」困境其實也涉及第二個層次的問題。總統忽略了政治上的往復溝通與實質審議,在一般行政決策上或許還可以用合法性控制或其他方式解消衝突,但由於服貿協議本身已經觸及「一個中國」原則,因此不可能單單用法律保留原則處理,而會碰觸到更深層的問題:主權的虛格化。
如果我們暫時拋開議會民主制或總統制這些概念原型,單純從授權來看,服貿協議談判的最終授權基礎來自於憲法增修條文,但是憲法本身所預設的中華民國主權,在兩岸談判中卻又要隱藏起來,那麼這樣的談判究竟是代表誰去談判?「兩岸」和「國際」是互斥的概念,一旦鎖進兩岸「地區」對「地區」的一中架構,就不可能出現臺灣的國家主權。本質上,將兩岸交流的進程置於區域經濟整合的架構底下,便揭示了臺灣和中國是朝向一個政治統合的未來前進。以兩岸談判來進行區域經濟整合,就等於排除了其他國家參與這個經濟整合過程,就不是國際合作。既然兩岸並非對等的主權國家,無論從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角度或是從《中華民國憲法》的角度,臺灣都只能是一個地區,臺灣人民無論選了多少次總統,仍然無法產生真正的「主權者」,這種正當性危機是無法透過權力分立體制來解決的;更不要說這套權力分立體制本身尚有決策權力無法正當化的制度性障礙。總括而言,服貿協議涉及的「自我治理」困境至少有兩重:第一重是權力分立體制無法有效正當化決策權力;第二重,也是更深層的,是主權虛格化帶來的危機。
三一八運動在外觀上,似乎是總統職權行使的問題,或行政立法相互制衡的問題,但真正的癥結在於《中華民國憲法》所表徵的主權在「兩岸協商架構」加上「區域貿易整合」的兩種矛盾邏輯交集下,徹底虛格化。對於主權的焦慮(第二層次)和對於總統權力運作的不信任(第一層次),重疊在一起,彼此互相增強,形成一個雙重螺旋結構,最終引導出人民的占領行動。
二、總統成為憲法的「例外狀態」
認識到這個雙重螺旋結構,再回來看:馬英九當時集黨主席和總統於一身,可以號令國會和行政院貫徹其政治意志,在權力的穹頂上已經達到最高峰,但如果他已經擁有臺灣最強大的政治權力,為何這樣的權力無法克服中華民國主權虛格化的困境,反而開啟了總統權力擴張的現象?民選的總統無法將中華民國主權實體化?那麼民主化歷程中不斷強調的「主權在民」論述,到底發揮了什麼樣的作用?
總統,在臺灣過去六十六年的歷史當中,扮演了極為重要的角色。無論是蔣介石、蔣經國、李登輝、陳水扁、馬英九,從戒嚴時期到民主化階段,乃至於政黨輪替兩次後,總統都是臺灣政治社群的最高權力象徵。在戒嚴時期,蔣介石以政治實力凌駕於《中華民國憲法》之上,不但透過國民大會老代表修改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變更了「總統不得連選連任超過一次」的憲法規定,也透過大法官解釋,實質改寫了國會(國民大會、立法院、監察院)的組成方式,讓老代表們可以不經選舉、直接延任,甚至不需到達法定人數就可以召開會議。當老代表逐漸凋零之際,還可以直接由原省籍同鄉遞補名額,最後迫不得已才小幅度放寬,變成臺灣地區進行增額補選。由此可知,戒嚴時期的憲政史就是圍繞著總統的統治權為核心,打造出中華民國的「超級總統制」。
民主化之後,李登輝所主導的修憲,仍然延續了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的「外加附款」形式,以「增修條文」覆寫憲法本文。擔任總統初期,李登輝遭遇許多現實政治上的挑戰。如果當時推動制定新憲法,勢必遭遇嚴重的反撲,甚至是軍事政變,《中華民國憲法》因而成為李登輝和國民黨舊勢力的緩衝點。老國代、老立委雖然因為野百合學運的衝擊而下台,但國民黨舊勢力透過《中華民國憲法》本文將中國「法統」霸權(jurigeneratical hegemony)恆久封存(entrenched)。因此,雖然形式上已經宣布動員戡亂時期終止,但憲法本文仍舊留存,代替老代表們來象徵「全中華民國」的續在。接下來,李登輝推動了五次修憲,從中央民意代表全面改選、增加總統國安大政方針權、總統直選、行政院院長任命權,到凍省,都是透過修憲,將威權時期的「超級總統制」合憲化,將總統塑造為民主化之後中華民國的最高權力核心。陳水扁和馬英九雖然分別屬於不同政黨,但是同屬這套體制的受益者與實踐者。從一九九一年廢除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以來,歷經七次修憲,沒有一次由人民發動,無怪乎不論怎麼修,人民不會認為這套憲法是自我治理的基本規範,充其量只是最高權力核心制定的權力遊戲規則。這種修憲最終是為了保存法統,即便人民直選總統,也不可能衝破憲法本文裡「全中華民國」的「天花板」(ceiling)。憲法權威來自於「法統」而非國民主權,因此
修憲無法續造憲法權威,反而創造了憲法威權主義(constitutional uthoritarianism)。
書籍代號:0GGK0234
商品條碼EAN:9789865727345
ISBN:9789865727345
印刷:黑白
頁數:408
裝訂:平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