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者:林欣誼
出版品牌:好人出版
出版日期:2021-03-31
產品編號:978986997765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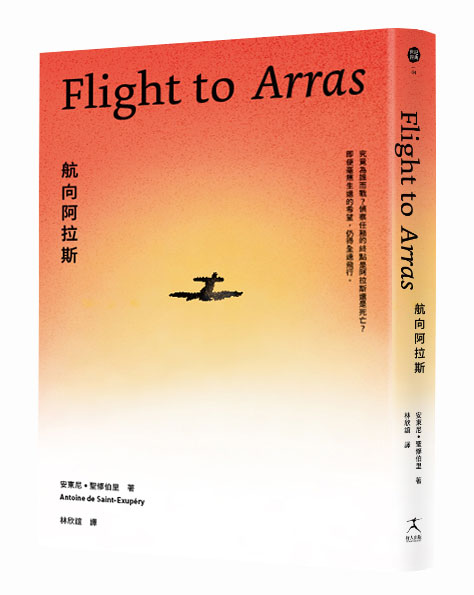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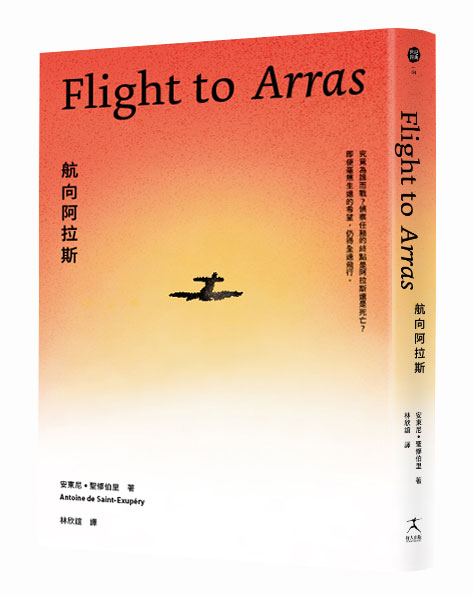

《小王子》作者安東尼.聖修伯里的自傳類小說
讀懂《小王子》前的必讀之作
「死亡,在這團混亂的局勢中,已不算什麼。」
戰火陰影下,面對毫無生還希望的偵察任務,聖修伯里不是害怕,只是有點憂愁而已,因為他所愛的人已先他而死去。
毫無意義,卻別無選擇的飛行任務
就像試圖用一杯水來撲滅森林大火般
1940年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安東尼.聖修伯里於法國戰役中擔任飛行員、實行偵察任務,卻眼見同袍一一殞落在戰火中,短短幾日內,僅有23人的偵察隊伍便犧牲了17人,每次飛行都無疑是一趟有去無回的死亡之旅。而他,即將啟航……
本書寫於1942年,作者將幾個月的飛行濃縮紀錄成一趟「航向阿拉斯」的旅程,描述任務期間親眼目睹的戰爭景象,呈現槍林彈雨、殘酷無情的現實世界,透過幽微敏感的筆觸書寫對戰爭的反思。
面對無力抵抗的長官指令、習以為常的死亡消息、有去無回的偵查任務,身為法軍成員的自己與夥伴們,為何要義無反顧地撲向死亡?死亡到底是什麼呢?生而為人的意義又是什麼呢?在無情蔓延的戰火中,頹敗毀壞的城鎮、無家可歸的人民、出生入死的軍隊同伴,無不刺激著安東尼.聖修伯里思索人類文明、生命真義與死亡的價值。
這不是一本飛行員所見的紀實回憶錄,而是對於生命意義、人類文明的深度思考,關於身而為「人」的我們,如何在失敗、死亡當中領略犧牲與愛。
「人人都是蠢蛋。這位不知道我的手套在哪裡的勤務兵,引爆這場瘋狂戰役的希特勒,還有參謀總部裡那些滿腦子低空偵察任務的傢伙,都是。」
——安東尼•聖修伯里對二戰法國戰敗的深沉控訴,因為這段話,本書於1942年出版後,即被德國當局查禁 。
安東尼•聖修伯里Antoine de Saint-Exupéry(1900-1944)
法國貴族後裔、作家、詩人和飛行先鋒,獲得了法國數項最高榮譽的文學獎項,以及美國國家圖書獎。他最為人所知的是創作了風爢全球的《小王子》,以及《南方信件》、《夜間飛行》、《風沙星辰》等書。在《小王子》出版一年後,在一九四四年七月三十一日執行一次偵察任務時失蹤。
林欣誼
英國華威大學翻譯學系碩士,曾任科技業數位行銷與國際業務。以商管專業維持生活,以閱讀文學餵養心靈。旅居歐洲數年,現為兼職譯者。
所謂該我們上場,指的是我們被分派到一個偵察任務。時間是一九四○年五月底,正是我軍大撤退,兵敗如山倒的災難之時。飛行員前仆後繼地犧牲,就像試圖用一杯水撲滅森林大火般,人人視危機和風險的概念如耳邊風。整個法國軍隊只剩五十支偵查小組,每三人為一組:飛行員、觀測員、射擊士。五十支偵察小組中的二十三支組成了我們的單位: 2-33聯隊。三週內,二十三支隊伍只剩下了六支。我們聯隊就像是風中殘燭般,快速消融如滴蠟。昨天我和嘉瓦中尉聊天時提到:「我們戰後再說吧。」話才說完,嘉瓦便回:「上尉,你還覺得我們能活過這場戰爭?不會吧?」
嘉瓦沒在開玩笑,他嚇壞了。我們很清楚,除了將自己投入這場如同森林大火般燃燒的戰爭中,別無選擇。就算這一切毫無道理可言。整個法軍只有五十位偵察機組員,整個法國軍隊的作戰策略都落在我們的肩上。戰爭的森林大火正猛烈地燃燒,而有人卻希望能用幾杯水來撲滅它。這幾杯水當然註定是要被犧牲了。
就是這樣了。誰會想抱怨呢?我們之中除了:「長官,非常好!是的,長官!謝謝,長官!沒錯,長官!」什麼時候聽過其他的回答了?在法國即將步入終戰的這段期間,有種感覺籠罩著我們,一種荒謬感。所有事物在我們身邊一一裂解,崩塌陷落。這崩壞感太過徹底,以至於連死亡本身對我們而言也變得荒謬。死亡,在這團混亂的局勢中,已不算什麼。我們自己也不算什麼。
杜特和我到了少校的辦公室。少校名叫阿里亞斯,我寫這篇文章時,他人還在突尼斯指揮2-33聯隊。
「午安,聖修!哈囉,杜特!坐。」
我們坐下。少校在桌上攤開一張地圖,轉身對下屬說:
「幫我拿氣象報告來。」
他坐著,不斷用鉛筆敲桌子。我看著他,他臉色憔悴,幾乎都沒有睡。他最近不斷地開車,整晚來回奔波到臨時參謀總部,也被召去師部和旅部,向軍備補給站強烈抗議並爭取他們答應要給但總是食言的裝備。這期間他的座車常塞在車陣中動彈不得。在我們被敵軍逼得四處竄逃,處境像是在冷酷的法警車中痛苦掙扎的壞蛋時,他負責督導我們機組員最後一次撤退和最近一次的移防。阿里亞斯成功地救回了我們的飛機、貨車,以及空軍聯隊軍需品和文件檔案。他看起來疲憊不堪,氣力用盡。
「嗯…」他說話了,手上的鉛筆不停地敲打桌面,眼睛仍然不看我們。
沉默了幾秒後,少校再度開口:「這他媽的太爛了。」他聳聳肩,總算說出心裡話:「他媽的爛任務,但參謀總部說要這樣幹,就是要這樣幹。我和他們吵,但他們還是堅持要做……就是這樣。」
杜特和我坐著,望向窗外,這裡的樹枝也同樣隨著微風搖動。我聽見母雞的咯咯啼叫聲。我們的戰情室借駐在一間校舍中,少校的辦公室設置在一間農舍裡。
要用幾頁虛偽的文字來描寫明媚的春日、正在熟成的果實、穀倉旁滿院子長得胖嘟嘟的小雞、抽高的麥穗,來對比近在咫尺的死亡,是再簡單也不過了。但我不會這麼做,因為我不認為平和的春日背後組成的是死亡的概念。為何生命的甜美到頭來會是一場諷刺?
然而當我望向阿里亞斯的辦公室窗外,一個模糊的想法卻確實地閃過腦中。「春天已死。」我喃喃自語,「季節錯亂了。」我曾飛越廢棄的打穀機和收割機,看見摩托車被丟棄在路邊的溝渠中。我也曾偶然到達一座積水的村莊廣場,廣場上的水龍頭――所謂的「水源」――大開,水流源源不絕地湧出。
突然間,一個特別荒謬的影像出現在我腦海:我以為時鐘壞了,所有在法國的時鐘都壞了。教堂尖塔上的鐘、火車站內的鐘、廢棄空屋煙囪上的鐘、納骨塔裡的鐘。「戰爭啊,」我對自己說,「戰爭讓時鐘不再轉動,作物再無收成,農具車無人上油保養。而水源呢,本來人們汲水、送水以解渴、以洗滌村裡婦女週日禮拜時穿的美麗衣裳,現在這些水卻四處流淌,淹沒了村莊教堂前的廣場。」
至於阿里亞斯,講話的語調就像病床旁的醫生。「嗯,」醫生邊說邊搖頭,「這狀況很棘手。」 暗示著你該開始寫遺囑,要有心理準備,即將離開身邊親愛的人而去。不用問也知道,杜特跟我想的一樣: 阿里亞斯意有所指,正是要讓機組員犧牲。
「再說了,」阿里亞斯繼續說著:「現在事情就是這樣,再去擔心勝算有多少,也於事無補。」
有道理。一切已於事無補,而且這並非是誰的錯。開心不起來,不是我們的錯;要面對我們這些下屬而感到不自在,不是少校的錯;要發號施令,不是參謀總部的錯。少校因為荒謬的指令而心煩意亂,我們知道這指令很荒謬,而參謀總部也是知道的,他們為了下指令而下指令,在戰時,下達命令是他們的工作。大家都知道戰爭是什麼樣子:騎著駿馬的騎士――或者用現代一點的說法,摩托車騎士――負責傳達指令。在騷動和絕望之中,指令到來,這些英俊的騎士就像星星――捎來未來的訊息,從熱氣蒸騰的馬背上擲向軍隊,這些指令將重建世界的秩序――這就是戰爭的真實樣貌,或是被我想像力視覺化的戰爭呢。所有人努力地讓戰爭變得更像戰爭,誠心地遵守遊戲規則,讓戰爭本身或可心悅誠服地扮演它應有的角色。
為了打場像樣的戰爭,參謀總部下了這種犧牲空軍的命令。同時,沒有人願意承認這場戰爭打得毫無道理如同一場空,也無前例可循,就像斷了線的傀儡木偶,依舊被人拉扯著。
參謀總部慎重其事地發布了從未傳達的命令,並要求我們提供無法拿到的情報。空軍弟兄並不負責向參謀總部匯報戰爭的全貌,偵查隊員或許能測試或查證參謀總部對戰局的推測,但現在已沒什麼好推測的了。他們要求五十組偵察員描述出戰爭的全貌,但實際上,全貌並不存在。參謀總部做出這樣的請求,簡直就是把我們當成了一夥算命師。
當阿里亞斯說話時,我瞄了杜特――我的算命觀測員――一眼。後來他說了下面這些話:
「他們把我們當什麼了,竟把我們送去做低空偵察任務?昨天我才向某個師部的上校嗆聲,他也說了同樣的鬼話,『你告訴我,』我對他說,『告訴我要如何在五十呎的高度,以每小時七百哩的速度向你們報告敵軍的方位?』他看我的眼神好像認為瘋的是我不是他,『怎麼?』他說,『這很簡單啊,看他們有沒有射擊你就知道了。如果他們射你,他們的所在位置就是德軍啊。』你能想像嗎?那個大蠢蛋!」
有件事杜特很清楚,但上校可能忘了:法國陸軍從未看過法國飛機。我們大約有一千架飛機,散布在敦克爾克和阿爾薩斯之間。對地面上的人來說,等於是無垠天際中的微小存在,只要有飛機從我方領空轟隆而過,就被理所當然地當作是德軍;只要一聽到飛機聲,在看到飛機前就必須擊發所有的防空高射機槍,否則敵軍便會在眨眼之間投下炸彈。
「用他們的方法,我們倒可帶回極其珍貴的情報!」杜特說。
當然了,參謀總部必定會參考我們的情報,因為在戰爭的形式中,情報官就該運用情報。但就算是他們這種按圖索驥的作戰方式也失敗了。幸好,我們心知肚明他們是無法運用我們帶回的情報的。我們或許能帶回情報,但這些情報永遠無法送到參謀總部。道路可能阻塞、電話線可能被剪斷、參謀總部可能在倉皇中遷移,而真正重要的情報:敵軍的位置,不用等我們告知,敵軍大有可能會自行揭露。
舉例來說,前幾天我們2-33聯隊不斷撤退到拉昂附近,當我們正想弄清楚現在離前線距離多遠、還有多久又要被迫撤離時,一位中尉被派去向七哩外的陸軍司令報告軍情。在機場到總司令部的半路上,中尉的車碰上一輛壓路機,其後埋伏著兩部裝甲車。中尉的座車立即掉頭離開,但一陣機關槍掃射後,中尉被當場擊斃,開車的駕駛也受了傷。裝甲車是德軍,是他們讓我們學到所謂的「前線」在哪裡。
參謀總部就像是個橋牌好手,被坐在隔壁房間玩牌的人詢問:「你看我該怎麼出黑桃皇后這張牌?」這位好手怎麼可能在完全看不見那場牌局的狀況下,給出關於黑桃皇后這張牌的意見?
但事實上,參謀總部不能不給意見。此外,只要他們手上仍握有一定的兵力,他們就必須將其充分運用,否則他們就會失去對軍隊的控制,敵軍也會施加壓力,因此參謀總部便必須冒險。只要有戰爭,參謀總部就必須有所動作,就算這動作是盲目的。
儘管如此,當自己不在牌桌上,黑桃皇后的打法就實在難說。同時之間,我們學到――剛開始很驚訝,後來就覺得這是理所當然――一旦有了裂縫,機器就會停止運作。軍人們也不再有任務可以執行。
你或許會認為在撤退和落敗之時,會有許多急需處理的問題一一浮現,讓人難以決定該如何安排優先順序。但實際上,對一個落敗的軍隊而言,問題會自動消失。我的意思是,落敗的軍隊已被排除於牌局之外,一個不在牌局中的軍隊,要飛機、坦克、黑桃皇后有什麼用呢?你手握著王牌,猶豫著下一步,絞盡腦汁思考它的用處,然後在有機會贏的時候將牌孤注一擲。
通常人們認為戰敗時的局勢會是一陣喧鬧和忙亂,其實正好相反。喧鬧和忙亂是勝利的象徵。勝利是一種行動,是正在大興土木的屋舍。參與勝利之役的人們揮汗喘息,搬運著蓋房子的石頭。而戰敗的一方則疲憊不堪、支離破碎、百無聊賴,更感到一切徒勞無功。
我們被分派的偵察任務,從一開始就是徒勞的。殺戮隨著日子一天天地過去而不斷增加,徒勞無功的感覺也是。面對兵敗如山倒的狀況節節進逼,我們的指揮官只能拿出僅有的籌碼,祭出唯一的王牌。而坐著聽少校講話的我和杜特,就是他們的王牌。
少校正向我們概述下午的戰略行動。他要派我們先飛到三千英呎執行高空照相的偵察任務,接著飛至兩千英呎,到散落於阿拉斯廣大區域附近的德軍坦克營地上空進行偵查。他的語調從容不迫,像是在說:「然後你沿著右邊第二條街走到廣場,就會看到一間菸草店。」
除了「遵命,長官」,我們還能說什麼?偵查行動已徒然至此,我們的話語有多浮誇,這偵察任務就顯得有多麼徒勞無功。
我自己的想法是:「又一組被拋棄的飛官。」我和自己對話。在腦海一片混亂、被各種事物糾纏之時,仍和自己說,我必須等待。如果我們飛得回來,且當晚還活著,那就到時再來思考。
如果我們還活得成的話。當偵察任務不「棘手」時,三架飛機裡可能有一架回得來。這比例在任務棘手時自然不一樣。但我並不是在計算我的存活機率。坐在少校的辦公室裡,死亡之於我,既不莊嚴、不壯麗、不壯烈也不辛酸。死亡對我來說只不過像是錯亂的象徵,是失序的後果。空軍聯隊失去我們,就有點像是在轉接火車時遺失行李一般。
並不是說在戰爭、死亡、犧牲以及法國的議題上,我除了現在寫的內容之外沒有其他的想法。但坐在少校的辦公室,我的思緒失了方向,言語含糊。我的想法自相矛盾,對真理的看法四分五裂,而我只能盡量檢視一片又一片的碎裂思緒。「如果我還活著,」我對自己說,「我今晚就會好好想一想。」令人喜愛的夜晚啊!讓言語消逝也讓事物甦醒的夜晚,在白天破壞性的分解完成之後,讓所有真正重要的事物重回完整與圓滿,讓人們重整脆弱的自我,與樹木一同平靜地成長。
許多家庭在白天裡爭吵,但夜晚讓吵架的人們重新找回愛意,因為愛本身已超越了言語所能表達。男人在星空下斜倚著窗,再度為明天的生計、為身旁熟睡的妻子,也為脆弱的、細緻的、意外的一切負起責任。愛不是一種思想,而是一種存在。我坐在阿里亞斯面前,渴望著夜晚,渴望自己能夠重生而成為值得被愛之人。當夜晚來臨時,我將為文明、為人類的命運、為祖國的袍澤之誼而思考。夜晚,或能讓我往某種強烈但一時半刻無法確切定義的目標飛奔效力。夜晚,讓我有機會能修復自己混亂的語言能力。我如同詩人般渴求夜晚的到來,如同一位真正的詩人,感到自己被一種模糊而強大的東西占據,為了捕捉它,詩人奮力地試圖從圍繞著這東西的重重壁壘中拼湊出此物的形象,從影像中的圈套去進行捕捉。
當我坐在那裡期待著夜晚降臨,我一度感到自己似乎被上帝的恩典所遺棄。確定的是,我會和杜特一起光榮地完成任務。但我們執行任務的方式,卻好似心中已無神明,卻仍要將一場不再有意義的古老酬神儀式發揚光大。我告訴自己,等待夜晚來臨吧!如果到時我還活著,我將走上穿越我們村莊的那條道路,將自己單獨而安全地隔絕於我所愛的孤寂裡。如此,我或許就能領悟,為什麼該去死的人,是我。
書籍代號:1ACC0004
商品條碼EAN:9789869977654
ISBN:9789869977654
印刷:單色
頁數:296
裝訂:平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