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者:葉旻臻
出版品牌:燈籠出版
出版日期:2024-07-31
產品編號:97862697926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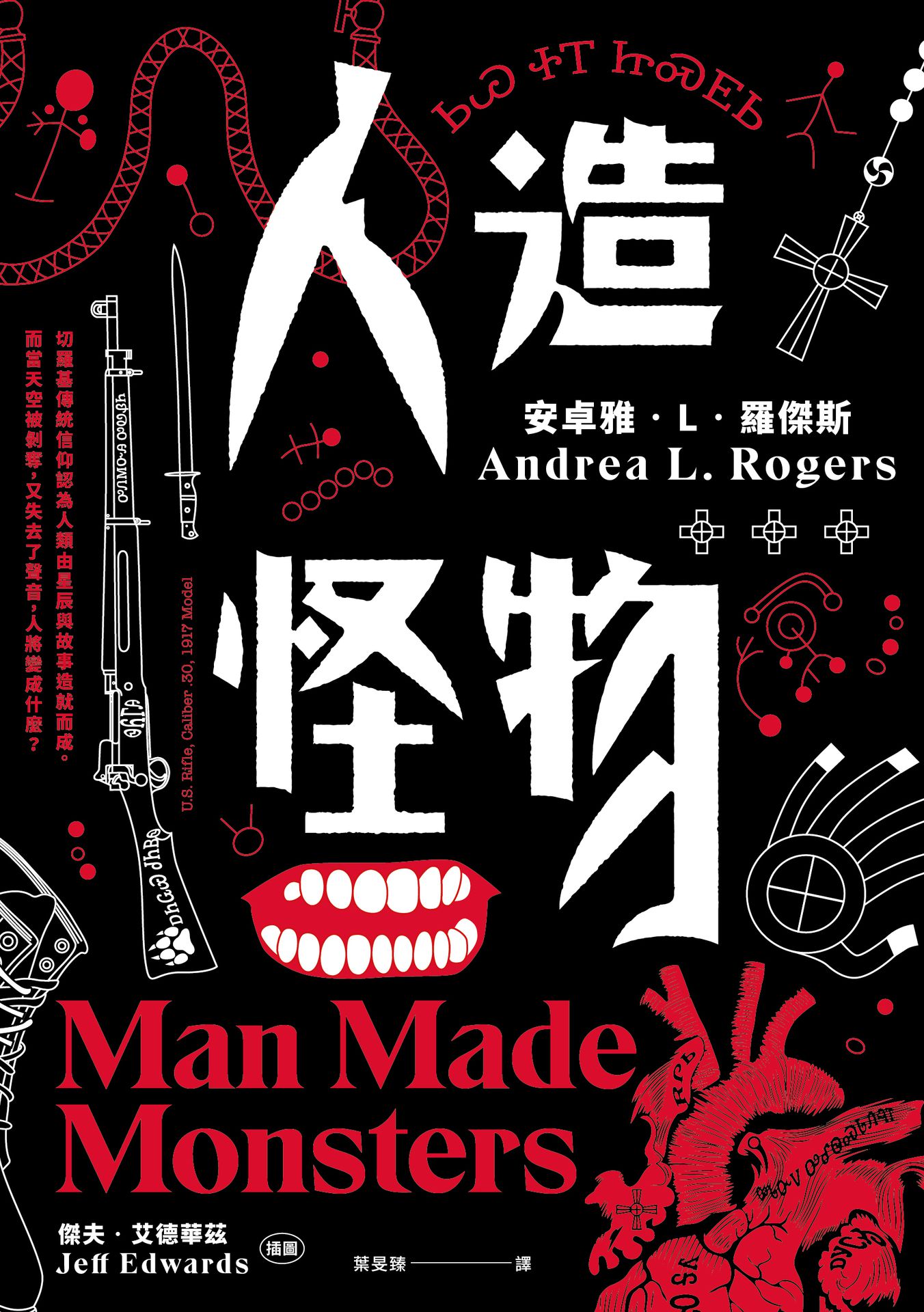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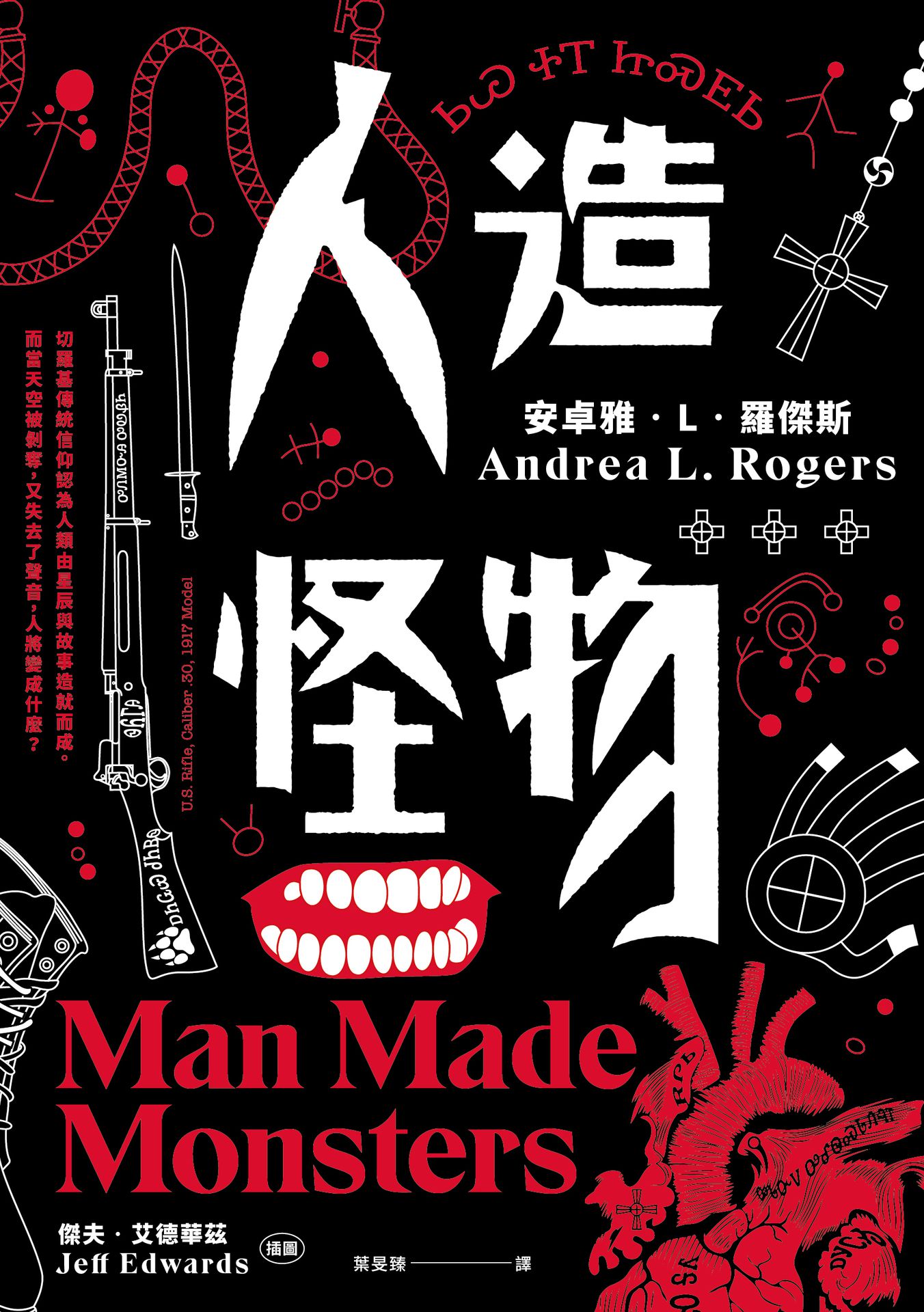
◀◀◀
被迫遷徙的血淚之路,
十六歲的少女,一夕之間成了吸血鬼……
從1839年到2039年,從過去到未來
18篇來自一個印第安切羅基家族的怪奇故事
狼人/鬼魂/羊男/鹿女/外星生物/喪屍
復活實驗/時空穿越/記憶抹除/植入研究
代代光怪陸離的切羅基家族史,
頁頁控訴著兩世紀以來的暴力與創傷……
►►►
▌榮獲2023第48屆國際素養協會(ILA)青少年文學組首獎、2023第8屆Walter Dean Myers Award青少年文學組首獎、2024第10屆美國印第安圖書館協會(AILA)青少年文學獎等眾多獎項
▌《出版人週刊》、《華盛頓郵報》、《書單》、《號角圖書》、《紐約公共圖書館》年度選書
▌切羅基文字復興藝術家以切羅基音節文字為元素創作的18幅精美插畫
∞∞∞各界推薦ᎣᏍᏓ∞∞∞
⧫透過切羅基視角呈現的一場穿越時空壯麗之旅!這本短篇小說集不僅僅有魔法、恐怖和奇幻元素,更充滿了聲音和廣度。引人入勝,妙趣橫生,同時極度嚴肅。這是一本滿載怪物,文筆出色的書。
),入圍普利茲獎決選《不復原鄉》(Tommy Orange奧蘭治(‧湯米——There, There)作者
⧫羅傑斯的書寫就像房子著了火,而能撲滅大火的,唯有她的文字。
),《紐約時報》暢銷書《唯一的好印第安人》(Stephen Graham Jones瓊斯(‧格雷厄姆‧斯蒂芬——The Only Good Indian)作者
⧫充滿力量、令人驚嘆、巧妙地運用原民元素!創意爆發,每翻一頁,我都覺得自己的牙齒變得更鋒利。
),《紐約時報》暢銷書《心鼓》(Cynthia Leitich Smith辛西亞‧雷蒂奇‧史密斯(——Heartdrum)作家
⧫這本書有吸血鬼、狼人、鬼魂、喪屍、海怪、外星人、鹿女和怪物(羊男),但書裡真正的恐怖來自種族滅絕和文化毀滅、家庭暴力以及性侵犯、校園槍擊、醫學實驗、流行病和生態災難。「條約遭人毀棄,我們被人形怪物追獵,以血和傷痛為食的怪物。」一篇篇故事讀起來像是家族流傳下來的記述;也像非常真實的推理小說。
《號角圖書》(——Horn Book)星級推薦
⧫羅傑斯運用自身切羅基的傳承,帶著深刻理解與敬意,很有巧思地打造出的這樣的恐怖和災難超自然創作,然而這本書飽含的敘事力量在於其強勁的筆鋒和問題意識:「這些喪屍與貪圖我們土地的士兵和拓墾者之間,又有何不同?」新穎、清晰的文字,交替使用第一人稱、第二人稱和第三人稱敘述,巧妙地探討了殖民主義的主題及其對幾代人的影響,讀起來既令人恐懼又扣人心弦。
《出版人週刊》(——Publishers Weekly)星級推薦
⧫對令人不安的歷史傳承進行一場毛骨悚然且一針見血的細緻探索。
(《柯克斯書評》——Kirkus)星級推薦
⧫令人炫目,多元視角,並且嚇人。
(《水牛城新聞報》——Buffalo News)星級推薦
⧫這一篇篇故事既精確又廣闊,說是挑戰界線,更像是用爪在挖掘,並試圖把一些東西抓回……儘管這無疑是一本恐怖小說集,然而源於家庭的溫暖核心,使它有了根基以及平衡。……融入切羅基語音節文字的插圖以及語彙完美地讓最終的成品呈現在讀者面前時——不管是成年人還是青少年——都感到吃驚且不安,彷彿瞥見了一個更大的世界,同時意識到似乎還有一個更廣闊的世界就在視線之外。
《書單》(——Booklist)星級推薦
關於作者
Andrea L. Rogers
安卓雅‧L‧羅傑斯
安卓雅‧L‧羅傑斯是切羅基國公民。她在奧克拉荷馬州陶沙市長大,於美國印第安藝術學院取得藝術碩士學位。她的短篇小說曾刊登於諸多文學期刊。合頂石出版社(Capstone)於二○二○年出版了《瑪莉與血淚之徑》(Mary and the Trail of Tears)。她的作品亦收錄於墨院出版社(Inkyard Press)的《你也是嗎?二十五個分享#METoo故事的聲音》(You Too? 25 Voices Share Their #METoo stories)、心鼓出版社(Heartdrum)的《祖先認證:給孩子的跨部落故事》(Ancestor Approved: Intertribal Stories for Kids),以及DK出版社的選集《同盟》(Allies)。她的繪本《當我們齊聚一堂》(When We Gather)由心鼓出版社推出。
關於插畫家
Jeff Edwards
傑夫‧艾德華茲
傑夫‧艾德華茲是奧克拉荷馬州威安鎮人,亦是一位得獎藝術家,服務切羅基國超過二十年。他是母語運動人士,曾進行多項將切羅基語帶上世界舞台的創作計畫。他曾就讀堪薩斯州勞倫斯市的哈斯凱印第安民族大學,取得人文副學士學位,並於塔勒闊的東北州立大學視覺設計學系完成藝術學士學位。他的作品幾乎全以切羅基文化為主體,相對於英文,更偏好使用切羅基拼音,以推廣切羅基語。他喜歡應用古老的文化概念,但是以現代數位工具來表現。
葉旻臻
自由譯者,譯作包括推理、科幻、奇幻等類型小說及非文學,譯有《少女A》、《不能贏的辯護》、《死亡預報公司》、《剽竊》、《魚夜》、《名為帝國的記憶》、《名為和平的荒蕪》等書。
賜教信箱:minjen.yeh@gmail.com
〈老派女孩〉
阿瑪‧威爾森
一八三九年玉米熟成月十五日
1839/07/15
身為切羅基人,絕不該仰賴人血維生,但是二八年華的少女有時就是會遭逢意外。我的名字是阿瑪,ᎠᎹ,意思是「水」,如果你發音正確的話;念不對,就變成「鹽」。媽媽是在獵月生下我的。
我們族人從德州逃往印第安領地的途中,某天我弟弟生病了。我們的切羅基族人和其他印第安人知道德州騎警緊追在後,不能耽擱,決定拋下我們繼續往北走。我抱著妹妹蘇珊娜,一同望著族人消失眼前。四周變得一片寂靜,媽媽駕著我們的篷車和兩匹馬駛離布滿凹溝的德州道路,盡其所能把我們藏在一叢茂密的矮牧豆樹後頭。我們打算在這裡紮營暫留,足夠我們蒐集到藥草並讓我弟弟威爾歇個息就好。然而計畫生變,半夜時分我們聽見德州軍隊經過,緊追我們族人後頭,僅僅相隔不到一天的路程。
爸爸一年前在墨西哥被抓走了, 但在那之前,媽媽年年懷胎。然而除了我們三個孩子,其他都活不久,而威爾有時候似乎也要撐不下去了。今年骨月出生的蘇珊娜, 倒是個健壯的寶寶。爸爸只有威爾森這個單名,但媽媽有珍妮‧菲許這個全名。
隔天,媽媽和我沒說多少話;我們的心在我們這個小家庭以及身陷險境的族人之間分成了兩半。威爾雖然睡得很多,但病情看起來正在好轉。我挖了一些植物根,並採集兔子草給威爾洗退燒浴,媽媽一面餵蘇珊娜,一面看顧他。媽媽好像在蘇珊娜不滿地哭鬧起來之前,就知道她需要什麼。有些媽媽就是這樣,能養出安靜的寶寶。
天黑時,蘇珊娜睡著了,媽媽把綴著兔皮滾邊的搖籃遞給我。我把搖籃放在篷車裡我的棧板旁邊,用自織的輕薄棉布整個蓋住。我們的馬嘶鳴起來,耳朵和身體轉向道路。我的雜色小馬目光在我和道路之間來回飄移,緊張地跺著蹄。我朝牠們看向之處望去,不久就聽見馬蹄聲和車輪聲,接著眼前出現一輛罩著骨白色蓋布的小型篷車駛出路面,往我們這裡喀喀而來。
握著馬匹韁繩的是一個瘦削蒼白的年輕男子。他把馬車拉到我們營火對面。他沒有出聲招呼或是揮手,只凝視著微微發光的煤炭,從篷車後頭透出餘暉,他看起來如幅剪影。
我提著蘇珊娜的搖籃,快步走去帳篷,放進藏起。婦女遭到劫掠販運的現象十分普遍,那是我最害怕的事。德州騎警和其他匪徒策馬直闖村子,尤其針對印第安人和西班牙人的聚落,然後劫走婦女、兒童、馬匹和任何可供他們利用或轉賣的東西,這種事層出不窮。
「媽媽,我們得走了。」我彎身對著帆布帳簾間悄聲地說。
媽媽皺起眉頭,威爾的眼睛微微睜開。「睡吧,小子。」她對我弟弟說。
媽媽拍了拍威爾,並站起來。她檢查了總是綁在腰間的小刀,然後跟著我往外頭走。
*
太陽從天際消失,留下一道道橙色和粉色。一個穿深色西裝的男人從篷車爬出來。他修成俐落三角形的鬍子和紅棕色髭鬚看起來和頭上的大禮帽幾乎連成一體。他穿得像個時髦公子,領子和袖口都綴有褶邊。他向我們脫帽致意。「晚安,小姐們。」
他用德語命令僕童去照料馬匹。
這個男人朝媽媽走近,先換成說柯曼奇語,再試了阿帕契語。我們只略懂一點,但他切換成西班牙語時,媽媽就叫我翻譯。她懂好幾種語言,但是只有切羅基語講得自在。我從族裡其他幾個人那裡學過西班牙語,也懂一點點德文,但是程度沒有好到能口語溝通。談論食物、水源和路況的話,我的西班牙文倒是足以應付。他說他是梅伊醫生,正在前往印第安領地途中。他提議用牛肉乾交換借用我們生的火。能夠在我媽媽煮的玉米湯裡添上一點肉,給體弱的弟弟補充營養,聽起來頗誘人的,於是她接受了。我感到不安,但無能為力。
臉上有雀班、眼珠近乎無色的年輕人把他的毯子鋪地於火堆旁。我看著他用髒汙的雙手鋪平毯子,感覺不太舒服。他伸展肢體,沉默地望進火焰。他從沒開口,似乎只接收命令。男人對他比了個手勢。「他不正常。」他解釋道。
「是啞巴?」我提示道,認為他選錯了詞。
醫生聳聳肩。
玉米湯煮好時,這個陌生人把自己的碗遞給媽媽,她幫他盛滿。「多謝。」他用德語道謝,並用銀湯匙攪拌湯。
「他不餓嗎?」我問道,朝那個少年點了一下頭。
男人的臉上慢慢綻開笑容,在他眼周稍稍擠出細紋。「一直都很餓。」他低聲用德語說,接著又說,「不,不,他不能吃玉米。」並挪到火堆旁安頓好。
「他不能吃玉米?」我用西班牙語再問一次。一時之間他面露困惑,馬上意識到我聽得懂他說的德語。他微笑點頭,然而他的笑令人感到不安。
我對媽媽解釋說那名少年不能吃玉米,她聽了皺起眉頭。她在錫杯裡裝滿了給她自己和威爾的湯,然後退入帳篷。我拿著我的錫杯走向篷車,看著那男人又攪拌湯碗好一會兒。我始終沒看到他動口去嘗,但他站了起來,伸展一下,繞到他的篷車後面不見了。看來他翻翻找找一陣之後,拿著一件黑色長大衣回來,蹲在火邊。我納悶他怎麼能忍受那樣的高溫,同時不讓袖子的褶邊著火。
「妳名字叫艾瑪?」
我皺著眉。雖然他自稱不通切羅基語,他還是專心聽媽媽和我說話,能夠依稀辨識出我的名字。
「阿瑪。」我說。
「艾瑪。」他又說一次,沒聽出兩者的差別。
醫生往火堆裡丟了根樹枝,看著它燃燒。他的嘴唇揚起一抹微笑,一副搞懂我的名字似地用西班牙語複誦著。「艾瑪,艾瑪,艾瑪。」
我皺起眉頭。我不喜歡他這樣練習我的名字。
「你們是印第安人嗎?」
我在黑暗中點頭。
他微笑。「跟妳媽媽說,湯很好喝。」他邊說邊站了起來。
他從口袋拿出一本小書和一枝鉛筆,說他也是個旅行作家,想說能不能問我幾個問題。
「明天吧。」我說,打算日出前就走人。
他的臉上倏忽掠過一抹慍色,但隨後點頭微笑。
他穿上大衣,也不管周圍多熱,從口袋裡拿出一只沒點燃的菸斗,向我舉起,說:「當然,就明天。」然後便消失在黑暗的草原。我轉身,發現那個少年在監視我,模樣就像藏身森林裡窺視的一頭狼。寒意爬上我的雙臂,令我汗毛倒豎。那晚我決定守夜保持清醒。我不想增添媽媽的擔憂,我知道她已經夠操心了。我們可以一早就離開,我再趁媽媽駕車的時候補眠。
然而飯還在吃,我便開始感到疲倦。我的嘴巴像塞滿了棉花,眼睛不由自主眨得愈來愈頻繁。我起身去洗杯子,瀝乾後要回到篷車上時整個人失去平衡。我發覺自己從來沒有這麼疲倦過。我爬進車裡,靠著上邊的側板,眼睛盯著火堆。我從夢境飄進又飄出,抵抗著睡意,腦中思索著導致我們走到這一步的原因,驅使我們族人離開德州的暴力壓迫。山姆‧休斯頓為我們爭取土地契約的努力與失敗。 我們的部族被驅逐,逃往印第安領地。
在我的噩夢中,德州軍隊又一次在路上策馬經過我們,一隊似乎永無止盡的武裝白人,綿延不絕的旗幟、大砲、槍枝和刺刀,展示在我們前後的道路上。
媽媽的短促一聲尖叫把我驚醒。我坐起身環顧四周。營火仍在熊熊燃燒,但是四下無人。我從篷車爬出來,差點摔倒,跌跌撞撞地往帳篷的方向去。一到門口,我就癱倒了。那個高大的男人站在媽媽上方,在她的喉嚨捅了一根針。他旁邊站著那個少年,小心翼翼地拿穩一個長形玻璃罐,連接著一支玻璃針筒的末端,注滿了我媽媽的血液。我掙扎地爬起身,並努力保持清醒。
隨著血液流入罐裡的速度減緩,我媽媽的呻吟聲也隨之變得微弱。那個男人抽出她頸上的針,任由她摔倒在地。他的襯衫釦子解開到肚臍,白色的領襟濺上血跡,胸前的毛髮刮得乾淨。他將針深深刺入他的心臟,整罐血都注了進去。我逼自己撐著手肘爬行,試著爬向媽媽身邊。
那個男人嗥叫,發出一種非人的恐怖聲音,幾乎擊垮了我的勇氣,但我看到威爾躺在媽媽身旁哭泣,他纖長漂亮的睫毛滴著淚水,嚇得顫抖不已。那禽獸對同行的少年吼了些什麼,他便朝我身側踢了一腳。我躺在原地暈了過去。等我睜開眼睛時,那男人已經拔除他胸口上的針。他用一條手帕壓著出血點,瞪視著我。媽媽沒再發出聲音,一動也不動。
我感到肋骨前所未有地疼痛,但我還是開始往弟弟爬去。
那個男人又對少年說了什麼,於是他彎身抓起了威爾,一手將他按在自己肩膀上,一手拿著與大型針筒相連的玻璃罐。
「威爾!」我尖聲喊道。
那個穿著時髦的男人彎下身,左手強行拉著我坐直,右手狠狠甩我巴掌。
我舉起雙手阻擋,試圖退開,但他在我面前蹲下來,雙臂環住我的肩頭,把我拉向他。他枯朽的氣息吹在我頸上感覺很乾燥,比一般人的呼吸更冰冷。
「安靜,」他悄聲說,將我的頭往後按,然後停頓了一下。「這是傳統方法。」他的牙齒咬進我的喉嚨。我感覺到皮膚、血管和肌肉撕裂了,他剃鬍過的臉刮擦著我的皮膚。我的脖子右側微微鼓動。我盯著帳篷裡燈籠的光芒,似乎更加閃耀,我痛到眼前的燈籠彷彿燒了起來,像明亮的太陽。接著光線開始消逝。但願如此我們就能一家團聚了。我爸爸也死了嗎?下一個肯定輪到威爾了。突然間,我聽到蘇珊娜在哭。
那邪惡的醫生露出笑容。
沒多久,少年帶著我哭嚎不止的妹妹進到帳篷來。
「是要喝的嗎?」他問。
「要賣的。」那男人回答。
連緩解片刻的機會都沒有,對這種人求饒是無用的。「現在妳要變得跟我一樣了。」我不想要,但是已經沒了聲音和力氣。他尖利的牙齒又撕扯一陣我的喉嚨,然後將我放下。他從長褲口袋取出一把剃刀,在胸口稍早用針刺出的洞孔上割出一個十字,就在他心臟上方。他躺到我身邊,輕撫著撥開我的黑色長髮。他把我拉近他,將我的嘴靠在他的乳頭附近,粗粗的毛根戳刺著我的臉頰。
「喝吧。」他耳語道。
他將我的嘴唇壓到他的乳頭上時,我奮力抵抗,但是鹽和銅的味道仍然觸及了我的舌頭。醫生的雙手按著我的頭抵在他的胸膛,直到我開始吮飲才放鬆力道。我感覺頭暈腦脹,想著媽媽餵哺蘇珊娜的模樣。我陷入迷惑之中,血的味道起初嘗起來像鹽水,接著變得如同乳汁。儘管心中驚駭,我發覺自己仍然不住吸吮,同時飢餓給了我一股為了滿足血欲而生的力量。
那頭怪物將手指伸進我的髮辮,鬆開皮革髮繩,讓我的頭髮散在肩上。他用德語悄聲說了些我不懂的話。飲血時,一陣顫慄在我的皮膚上擴散,他觸碰到我的任何地方都又麻又刺。只有對他血液的渴求能抑制住於那股感覺。我的手伸到他背後,更用力吸吮起來,牙齒蠢蠢欲動地想咬進他的血肉。
他溫柔的撫摸停止了,抓著我的頭髮將我拉開他的胸膛。我也反手抓他,拚命想回去繼續飲血,他用超自然的力量反擊,摔得我仰倒在地,還撕破了我的襯衫前襟。
「別動,我的艾瑪。」他柔聲說,剃刀突然伸到我的耳邊。刀尖陷進我耳朵和頭髮之間的皮膚,彷彿要將我剝皮。
我靜止不動。
他在我胸上割出兩條細線,壓到我身上開始吸吮,我耳中的心跳怦怦作響。餵我之前,他已經將自己的心臟裡灌滿我媽媽的血,也喝了我的。現在感覺他像是要把餵出去的又吸回大半。我體內的緊繃鬆開了,彷彿從高處墜落,掉入一池溫水。我閉上雙眼,準備迎接死亡。這股欣快來得出乎意料,神祕莫名,如同黑暗中的暖陽。我注意到他停了下來,頭擱在我胸上歇息。
我別開頭,並再一次感受到媽媽死亡帶來的震驚。那名少年站在她身旁,手裡擺弄著一把大刀。他跪下去拉起她的裙子,雖然背對著我,但我知道他在做什麼。我聽過有些屍體被德州騎警這樣剝了皮,印第安人的頭皮有時候被當成戰利品,有時也像動物毛皮一樣拿來販賣,有時則用來紀念某場壓根沒發生過的印第安人襲擊事件。媽媽被剝皮的過程中失的血比一般人少。我正在想等等他們剝我的皮時,我是已經死去,還是處在垂死邊緣。
我的心思在帳篷裡外飄蕩。聽著蘇珊娜從醫生的篷車裡傳出的憤怒哭嚎,我的眼裡盈滿淚水。我媽媽美麗濃密的黑髮從那名少年的腰帶垂下。他拿著刀子比向我。我抬起手,摸摸耳上被那頭怪物剃掉一小塊頭髮的位置,我的手因此沾上一點點血。
醫生坐起身來,對著少年搖搖頭。他用一塊汙損的水牛皮披毯掩住我撕破的上衣。
「我們走吧。」他站起來,然後切換成德語對少年說了些我聽不懂的話。少年皺著眉頭,伸手摸向腰帶上的刀子。
接著兩人都靜止不動。
「快去啊!」那怪物發出嘶聲。
少年轉身離開帳篷。那白人輕而易舉地將裹著水牛皮的我拉起來,扔到營火邊。我時而清醒,時而昏迷,聽見他和少年翻動著我們的行李。醫生抱著蘇珊娜走來走去,想哄她別哭了。她的哭聲停止時,我放棄掙扎,沉入夢鄉。
我在火堆旁睡得很不安穩,開始覺得全身像爬滿螞蟻,咬得我痛如火燒。我勉強睜開眼睛,只看見自己的皮膚反射火光,沒有螞蟻。後來,我失禁了,弄髒了我的衣服和染血的水牛皮毯。肯定是那個醫生把血痢傳染給我了。如果真是如此,在沒人照顧的狀況下,不出幾個小時,我必定會如願一死了。我的下顎和嘴唇都在痛,全身打著寒顫。接下來的整夜,我昏迷不醒。
將近黎明時分,我醒了。火焰中油脂劈啪作響,焚燒我家人血肉產生的濃煙鑽進了我的頭髮和衣服。我瑟瑟發抖。我從沒感到如此寒冷,儘管水牛皮毯散發著穢物的惡臭,仍是我唯一的溫暖撫慰。
又過了一陣子,我再次醒來,撐著顫抖的腿站起身。這燒死我家人的氣味傷透了我的心。我們原本應該要和媽媽的族人團圓:她的家人,她的兄弟路易斯‧菲許與他的妻子──而不是死在德州。看樣子,那男人和少年一搜括完所有可以利用或轉賣的東西,就把我家人的屍體裝進篷車,推到營火上。火堆旁插著一支柯曼奇長矛。
我搖晃不穩地走過去,從地上拔起長矛,用它戳撥冒煙的毯子,試著數算漸熄的火中骷髏頭的數目。全都緊挨在一起,團團焦黑的肉塊,看起來像是我弟弟和媽媽兩雙小小的、被燒毀的腳,在灰燼中幾乎不成人形。似乎沒有另一具較小的屍體。我媽媽的刀在灰燼中被燒黑了,刀柄也不見了。我把它撈了出來,從水牛皮毯上割下一條皮革包住,權作刀柄。
我倚靠長矛上,凝望著煤炭最後的火光。地平線上,太陽開始從我們來的方向燃燒,我瞇起眼睛。陽光就像帶著火的沙塵,灼痛我的雙眼。我把牛皮毯拉高護住臉。
陽光普照之際,我發現自己看不清東西,幾乎像在夜裡。最終,我會學著該如何在白天保護自己。暴露在陽光下導致我們需要更頻繁飲血。馬匹的足跡使我大惑不解,我不確定他們是繼續沿我們原本的路線前進,或是轉往墨西哥。
每個方向我都轉一轉,深深吸氣,感受風的味道。而東南方來的風,我只聞到死神的氣息。
死神搶走我們的馬匹,留下一支柯曼奇長矛,讓我們看起來像是死於柯曼奇族襲擊。死神跟隨著德州軍隊的篷車轍痕。我們的族人被德州軍隊追逐著,逃往印第安領地,逃向這個國家的另一端,而這個國家,相信只有死掉的印第安人才是好印第安人。
我開始走往東北方的那些聯邦州。
過去,我的族人會將死者的住屋燒掉。我不知道醫生是因為曉得這點而火化我的家人,或是單純想消滅他飲血的證據。我想到他搶走的小馬,那匹漂亮的斑點馬,我從小騎到大的。筋疲力盡的我想像著自己正騎在牠背上,低頭靠著牠的頸項哭泣。我沒有想到牠那奔跑時的身體流經多少豐沛的血液啊。至少現在還沒有。
我的族人已經往卡多湖周圍的灌木叢而去。樹叢中的黑暗就像歌曲般清晰地呼喚我。我想起族人,也掛念起被囚禁在墨西哥的爸爸。我想到我媽媽的家人,如果我不繼續前進,或許就永遠見不到他們了。
我走在清晨的日光中,感覺又冷又虛弱。這病讓我直打寒顫,又發著高燒。我感覺自己彷彿身處酷寒冬日。我經歷過幾次所謂的「藍色北風」風暴,當時溪水結成流冰、牲畜若沒有保護就會被冷風凍死,但是沒有任何一場風暴讓我像現在這樣凍寒入骨。發冷帶來的顫抖讓我行進的速度又更慢了。傍晚時我抵達濕地,筋疲力盡地開始在柏樹根之間踉蹌而行。我想起烏帖納,一種水中怪物,好奇像這種生著鹿角、形如巨蛇的怪物,是否曾經踏足如此這麼內陸之地。我聽人家說過,如果你看到烏帖納,那是世界即將改變的警示。對我而言,這警示來得太遲了。
長而瘦的樹根之間藏著許多巢穴。我找到一個大型的空兔子洞,裡面算是乾燥。我爬進黑暗的中心,一個讓動物等死的獸穴。
但是死亡從未降臨。
我想起過去生病時媽媽是怎麼照顧我的。有一次我發燒了,她用錫杯裝了冷水給我,求我喝下去。「喝吧,阿瑪。」她懇求道。然而或許我太過乾燥缺水,哭不出淚水。沒水,沒眼淚,於是我等待死亡,等待著與家人相聚。直到我睡著時,鹹鹹的眼淚自己淌下我的臉頰。感覺到濕濡的臉頰上吹來溫暖潮潤的空氣,我醒了過來,與一頭母鹿好奇的雙眼對視。牠棕色的眼瞳深暗,軟軟的粉色舌頭試探地伸出來,要嘗我臉頰上的鹽分。牠口鼻周圍的軟毛觸及我的臉龐,像輕輕一吻。我保持靜止,暫停呼吸。牠的舌頭舔得更快,喝著我臉頰上的鹽分和血液。牠舔舐的樣子飢腸轆轆,但我沒有移動。
終於,牠停下動作,轉開頭,我在那一刻出擊。儘管缺乏體力,牠皮膚下溫熱血液的香氣卻給了我意志力。我擁住牠的頸項,清晰地聽見我媽媽的聲音:「喝吧,阿瑪。」
我的下顎肌肉在睡眠期間變得強健,牙齒也變尖了。我咬穿了鹿皮,就像咬煮熟的菜葉一樣輕而易舉。溫熱的血液灑到我的臉上,牠往後退,狂亂地試圖逃離,但我繼續抱緊牠的頸子。牠搖搖晃晃,現在眼中充滿恐懼,然後就往側邊倒下了。牠的腿徒勞地在空氣中踢動,我溜到了鹿腿之間。
我飲血的方式缺乏效率。在當你真的很餓的時候,所謂的「傳統方式」不適合拿來給動物放血。而我真的很餓。我躺在牠仍有餘溫的屍體上,從牠脖子的傷口吸吮。直到再也喝不下的時候,我坐起來,感覺飢餓又噁心。這頭鹿可以讓好幾個家庭飽食多日。我們有多少次在鍋壺空空如也時,亟需肉食時,感謝有人為我們帶來宰好的鹿?想到要把鹿肉留在地上腐爛,真是令我作嘔。
於是,我用尖牙咬進牠柔軟的腹部。喝飽之後,我的手更有力了,能夠輕易撕裂牠的鹿皮。我的牙齒像刀鋒般輕鬆地切穿毛皮,然後是心臟和肌肉。我分開牠一根根肋骨,抓住牠微溫的心臟,易如反掌。我咬住並吸吮著那顆心臟。不久,我就把整顆心臟撕得破碎,吞食殆盡。我向後靠,看著自己瘋狂的傑作。如果換成一群狼,肯定會吃得更乾淨,更有效率。
生理上的反悔緊隨而至。吞下的鹿心和捨不得浪費的血一起反胃湧了上來。我在林地上嘔出猩紅的肌肉組織。我的身體劇烈且徹底地排空了。我爬離一片髒亂,默默等待。有了精力之後,也許我就能哭出來了。即使在白天,森林裡也是暗的,只是不如夜裡那麼黑。我會等到能夠離開的時候,去找衣服和更好的食物。我到水邊清洗,潛入水中七次,祈求得到淨化。我忍著飢餓,洗淨了浸血的水牛皮毯,然後抖開晾乾。
當太陽淡出天空,我開始走上那條能帶我找到死神醫生的路。我的族人在遠方,被一支嗜殺的軍隊追趕著。我的妹妹也在遠方,落入一頭怪物手中。而在這條路上,還會有人想毀滅我,偷走我的心去賣。
我的切羅基家人試圖逃往印第安領地是為了求生,為了和我們自己的族人不受打擾地活下去。然而,條約遭人毀棄,我們被人形怪物追獵,以血和傷痛為食的怪物。
血是濃鹽水──是大地的生命汁液。
水,血,力量,生命。
我過去對這些事物渾然無感,但現在它們就是一切。如今許多惡人可以供我飲血,我決定就這麼做。貪欲與渴望不知慈悲為何物。
我也變得毫無慈悲。
導讀
誰是怪物?
― 《人造怪物》中的群鬼亂舞/臺灣師範大學英語系優聘教授 梁一萍
老派女孩
人造怪物
一則非童話故事
無人區的地獄犬
歸鄉
瑪莉亞的無限可能
我和我的怪物
是月亮的錯
下雪天
阿瑪的男孩
美國掠食者
喬伊的顯化
水晶體
幽靈貓
永遠幸福快樂
鹿女
我從水中來
喪屍入侵露天汽車電影院!
致謝
切羅基詞語對照表
附錄 《人造怪物》故事一覽表
書籍代號:2UTR0001
商品條碼EAN:9786269792658
ISBN:9786269792658
印刷:黑白
頁數:424
裝訂:平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