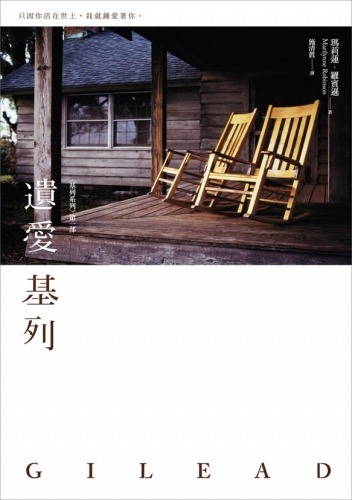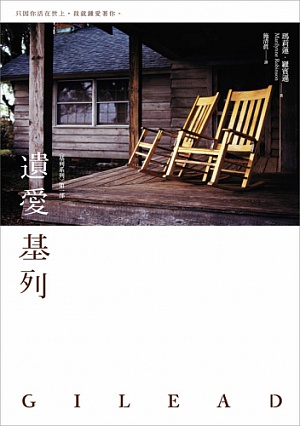導讀
浪子沒有回家 作家袁瓊瓊
二○○五年,《遺愛基列》得到普立茲文學獎。瑪莉蓮‧羅賓遜自己對《遺愛基列》的評價是:「這是一本安靜的書,既不憤怒、嚇人,也不古怪、詭異。」
她的這個評論,某種程度是個警告,警告讀者:你如果想看一本高潮迭起的書,想看一本驚悚刺激的書,那麼別來看《遺愛基列》,你一定會失望的。
如果在通俗看法裡,「憤怒、嚇人」,「古怪、詭異」意味著某種閱讀快感,羅賓遜似乎在表白:看她的書是不會有「快感」的。然而,意外的,這本被作者警告過不會帶來快感的書,卻非常好看,非常容易閱讀。她的字句簡淨單純,不飾華藻,然而所敘述的這個世界之美,卻透到骨子裡。讓人覺得,我們每個人的世界裡,其實同樣有這些美妙的東西,我們可以看到,如果能夠安靜下來。
是的,安靜。《遺愛基列》之安靜,不是無聲,反是眾聲隱然,那些繁複的多重多層次的聲音,由於安靜,成為渾然一體,成為生命的底層。我們每個人的生命都有這個底層,一般來說,我們聽不到也看不見,直到我們能夠安靜下來。
故事說不上有什麼情節。七十七歲的男主角講述他一生的故事。他家三代都是牧師,他自己年輕時結過婚,但是妻子難產死去。一併帶走了剛出生的孩子。他孤身活到六十七歲,遇見了第二任妻子。在晚年時結了婚,並且有了個七歲兒子。整本書是寫給兒子的一封長信,因為他預計自己可能活不到兒子長大。
某種程度,這封家書其實也是族譜,告訴兒子從何而來,血脈的根源是哪裡。
唯一可以算得上跌宕的情節,是他的好友柏頓最疼愛的兒子返家的部分。
羅賓遜在《遺愛基列》完成之後,又寫了《家園》。《家園》描述的便是《遺愛基列》中的柏頓一家。柏頓這個兒子的故事是主線。而二○一四年的新作,書名是《萊拉》,萊拉(Lila)是《遺愛基列》中男主角第二任妻子的名字,或許這本新書也與《遺愛基列》存在平行關係。
幾乎同樣的故事,羅賓遜一說再說,用不同的方式。這決不是找不到新的素材,而應當是整個故事是某種原型,能夠產生的意義太多。
在《遺愛基列》中,明顯可見的原型是「浪子回家」的故事。
聖經中,「浪子回家」是耶穌的一個譬喻。記載於《路加福音》第十五章第十一到三十二節。故事應當多數人耳熟能詳。小兒子愛玩,要求分家。把分得的財產揮霍得一乾二淨之後,回到家來。父親歡天喜地為他殺牛宰羊,還把最好的衣服拿出來讓他穿,最珍貴的珠寶拿出來給他配戴。一直跟在父親身邊任勞任怨的大兒子很不平,埋怨說:「我服事你這多年,從來沒有違背過你的命令。你並沒有給我一隻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樂。但你這個兒子,和娼妓吞盡了你的產業,他一來了,你倒為他宰了肥牛犢。」而父親回答說:「兒阿,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只是你這個兄弟是死而復活,失而又得的,所以我們理當歡喜快樂。」
聖經並沒有說浪子回家之後是不是就永遠待下來了。然而羅賓遜講的這個故事,浪子回家之後又離開了。而且,在《家園》裡,這個浪子再也沒有回來。
《遺愛基列》裡的浪子,就是柏頓的兒子傑克.柏頓。
傑克.柏頓與男主角同名。他出生的時候,男主角的妻女剛死不久,好友柏頓為了安慰他,把男主角的名字給了這個新生兒。用意不外乎是與好友一起擁有這個孩子,「我的兒子也就是你的兒子」。
但是這個傑克非常不成材,從小就壞點子特多,到處惹是生非,幹的都是所謂「好人」難以容忍的事。不小心把個窮女孩弄大肚子之後,他避不見面,逃到外鄉去。直到二十年後才回來。
在傑克初生之時,要接受洗禮,男主角身為牧師,必須祝福這個嬰兒。羅賓遜描寫男主角那時看著這嬰兒,感覺自己無法祝福他。或就因為這孩子與他同名,而他自己剛才喪了妻女,無法感覺這個名字是被祝福的,因之他就只走了個形式。之後,看到傑克種種劣跡,他總是會想到自己當初其實並沒有給他祝福這件事,而多少有一種心虛,感覺是自己那個不踏實的祝福害了他。
因之,至少是作者的觀點。浪子之成為浪子是有原因的,而浪子無法待在家裡,也是有原因的。這原因倒並非他生來「不被祝福」,而只是,浪子是不同於我們的另一種人。傑克的種種所謂劣行,在生命面前,其實是被容許的。羅賓遜在書中藉男主角之口說:「生命是莊嚴的,如果天主認為我們的過失不算什麼,那麼過失真的不算什麼。就算真的有些影響,相較於生命的莊嚴,過失也都微不足道,天主當然會將之一掃而空。」
這是包容和寬諒,給錯誤一個位置,因為生命的美好不在於不犯錯誤,而在於容許過失,容許錯誤。
在傑克再度離家前,男主角給了這個與自己同名字的男人真正的祝福。這段描寫極為平實簡單,不過六行,卻是全書最為有力量的段落。經文如下:「願耶和華使他的臉光照你,賜恩給你。耶和華向你仰臉,賜你平安。」他說:「主啊,請賜福給這位受人鍾愛的兒子、兄弟、丈夫以及父親。」他唸出了與自己相同的名字;同時,在祝福他人的時候,也祝福了自己。
聖經裡,摩西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有一支停留在基列,以放牧為生,生活非常艱苦。基列(Gilead)在希伯來文裡,因之便有了「艱難」的意思。書中人物居住在「基列」小城。羅賓遜虛構了這個地名,顯然不是全無用意。人生固然艱難,但是接受並且包容,艱難未始不是一種祝福。
內文摘錄
誠如先前所言,我大半輩子過得很寂寞,我將之稱為「慘澹歲月」,一說到我這個人,就非得提起那段慘澹歲月不可。那段日子過得非常奇怪,好像每個冬天都一樣,每個春天也大同小異。對了,還有棒球。我想我收聽了幾千場棒球賽,有時聽到一半就中斷,收音機一片沉寂,然後隱約傳出觀眾的歡呼,聲音平板微弱,幾乎難以察覺,好像迴蕩在貝殼中的虛空聲音。我喜歡想像球賽的進行,球場上千變萬化,我好像試圖拆解某個複雜的謎語,如果球滑向左外野,一、三壘有人,我就在腦海中讓跑者、捕手和游擊手同時移動,我好喜歡這麼做,卻也說不出為什麼。
我也喜歡採用同樣的方式來回想過去的談話。身為牧師,我最主要的職責是聽人說話,不管是嚴肅正經的告解或僅是傾訴,我都覺得非常有趣。我的意思不是說這些談話像球賽,我絕無此意,但若你想想球賽的抽象層面,比方說策略為何或是力量來自何處,你關心的似乎不是球賽了,而是雙方如何配合、他們有多需要彼此,以及球賽中真正的主題——生命力——將如何展現出來。我所謂的「生命力」,意思是某種「精力」(誠如科學家的用語)、或是「活力」。人們跟我說話時,不管談話的內容是什麼,他們口氣中蘊含著的一股「熾熱」,每每令我大為訝異。「我」的後面總是緊跟著「愛」、「害怕」、或是「想要」,對象可能是「某人」或是「什麼對象都沒有」,這其實無關緊要,因為他們的話裡面已經傳達出情感,情感像朵火花,繞著「我」打轉,散發出一股悲傷、愧疚或喜悅的氛圍,熱切而源源不絕。神職人員有幸目睹生命的這一面,這是一種大家很少提及的特權。好的講道是一方熱情的談話,眾人必須以同樣的心態聆聽。講道當然包括三方,即使最私密的思緒也是如此。一方是產生思緒的自我,一方是領受思緒並設法加以回應的自我,一方則是主,想來實在奇妙。我正試圖描述以前從未行諸於文的想法,寫得相當辛苦,我也有點累了。
有天聽球賽時,我忽然想到月亮呈螺旋狀運轉,隨著地球運轉的同時,它也隨著地球繞著太陽移動。雖然顯而易見,但我想了就開心。窗外是一輪明月,清澈潔白地高掛在深藍的天際,芝加哥小熊隊正大戰辛辛那提。
一提起貝殼的聲音,我想到兩句自己以前寫的詩:
掀開貝殼的螺旋,發現經文
隱藏在牧師的沙沙聲之下
詩的其他部分不值得記取,柏頓家的一個男孩不曉得為什麼到地中海旅遊,回來之後送給我一個大海螺,我一直把它擺在書桌上。長久以來,我始終很喜歡「沙沙聲」這個字眼,但除了將之納入詩句之外,我不曉得怎樣讓它派上用場。再說,在那段日子裡,除了經文、牧師和收音機的靜電噪音之外,我還曉得什麼?我還喜歡什麼?那時很多人閱讀《鄉村牧師之日記》,作者是法國小說家貝爾納諾斯(Bernanos),我很同情書中那個傢伙,但柏頓說:「喝酒喝出了問題。」他還說:「主只需要一個更稱職的人來填補那個空缺。」我記得自己整晚坐在收音機旁邊讀這本書,直到節目全部播畢,我仍繼續閱讀,一直讀到天空露出曙光。
有次祖父帶我坐火車到第蒙(Des Moines)看巴德‧弗勞爾(Bud Fowler)打球,巴德曾加入凱奧庫克隊(Keokuk)打了一、兩季球,祖父用他那隻好眼睛盯著我,一本正經地跟我說,世界上沒有人比巴德‧弗勞爾跑得更快、投得更準了,我非常興奮,但那場球卻沒什麼動靜,最起碼我當時是這麼想。沒人跑壘,沒人打出安打,也沒有失誤,到了第五局,醞釀了整個下午的雷雨終於降臨球場,球賽便宣告中止。我記得一開始下大雨,觀眾們就大聲抱怨,當時才十歲的我鬆了一口氣,但祖父卻非常失望,可憐的老魔鬼心中又多了一件憾事。我這樣稱呼祖父全無惡意,父親這樣叫他,母親也是,他在戰爭中失去了一隻眼睛,平常看起來也頗野蠻,但父親說,照他們那個時代的標準而言,祖父是位優秀的牧師。
那天他帶了一小袋甘草令我非常驚訝。每次他把手指伸進袋子,袋子就隨著他顫抖的手嘎嘎作響,聽起來像著了火。我當時特別注意這一點,但不覺得奇怪,當時我也多少認為,雷聲與閃電是造物者在跟祖父打招呼。祂似乎在跟祖父說,牧師先生,很高興在觀眾席上看到你,或者祂說的是,牧師先生啊,世上充滿悲悽之際,你為何跑來參加體育活動呢?母親曾說祖父總是交些「討人厭」的朋友,所謂「討人厭」是舊時代的用法,沒有不敬之意。祖父年輕時結識了約翰‧布朗*2*和吉姆‧蘭恩*3*,我真希望能跟你多說一些,但父親和母親不准提到堪薩斯州和內戰的舊事,這已成為家中的不成文規矩。從第蒙回來之後,我們就失去了祖父,或者說他迷失了自我,不管何者為真,幾星期後他就動身前往堪薩斯州。
我曾在某處讀到,一樣東西若和其他東西都沒有關聯,那它便稱不上「存在」。這番說辭完全出自假設,我不太了解它的意思,或許我壓根就不明白,但它確實讓我想起那個下午:空中沒有半個球,也沒有人盜壘、觸球或失誤,換言之,球場上毫無動靜。我覺得那場雷雨就是為了結束這種局面,好像有場火等著被澆熄,或是為這個無足輕重的場面注入一些爆發力。「天上寂靜約有二刻」(〈啟示錄〉第八章第一節),雖然雨下了遠超過半小時,但我記得天上似乎一點都不寂靜。「無足輕重」,這個字眼相當有力,祖父無處施展勇氣,也感覺不到心中的勇氣,想來實在可憐。
走筆至此,我察覺到自己的記憶力有點小題大作。祖父這個老傢伙穿著破舊的外套坐在我旁邊,雙手不停地顫抖,享受著甘草這種小小的奢侈,說不定就在那天下午,他對堪薩斯州的回憶讓他萌生了去意。(他想回去堪薩斯州而不是昔日佈道的小鎮,正因如此,所以我們花了好大的工夫才找到他。)巴德‧弗勞爾站在二壘上,一隻手套擱在臀部,目不轉睛地看著游擊手,我知道他打球時不喜歡戴手套,但我只記得那幅景象,從今以後一提到他,我也只記得他的那個模樣,因此,我也沒必要修正自己的記憶。多年以來,我一直從報上關心他的發展,直到有些人成立了「黑人聯盟」(Negro Leagues),我才失去了他的消息。
我高中和大學時是個不錯的投手,我們在神學院的時候也組了兩支棒球隊,時常利用星期六出去打球,我們把草地當成球場,也沒人曉得壘線在哪裡。我們打得開心極了,當年研習神學的年輕人都很傑出,我確信現在也是。
父親和我靜靜地沿著小路踏著月光而行,逐步遠離祖父的墳時父親說:「你知道嗎?堪薩斯州的每個人也看到了我們剛剛看到的。」那時我以為他的意思是,全州的人都看到了我們所目睹的奇蹟(請記住:我當時才十二歲),我以為父親在祖父墳邊的禱告感動了天父,所以祂特別降下恩典,或是祖父荒蕪的墳地忽然散發出榮耀的光彩,而全州的人都是我們的證人。後來我才明瞭,父親的意思是,太陽和月亮自行呈一直線,無關我們父子二人。除了《聖經》提到的異象或奇蹟之外,父親向來避談這類事情。
但那天晚上我走在他身旁,沿著崎嶇小路走過空曠的大地,我感到父親、我自己以及周遭充滿了一股神奇的力量,心中的歡愉著實難以言表。我真慶幸當時沒聽懂父親的意思,因為從那之後,我很少感受到那種全然的歡愉。這就好像做了一個甜蜜的夢,你在夢中享受了現實生活所沒有的奢侈,不管夢見了什麼,甚至帶點罪惡感或是有點害怕也沒關係,換言之,某些事情在現實生活中或許永遠不會發生,但你卻感受得到它們所引發的快感。誰曉得月亮會如此耀眼、如此令人心醉呢?父親雖然一語帶過,但我看得出他也有點感動,他得停下來拭去眼中的淚水。
祖父曾告訴我他看過的一個異象,當時他還不滿十六歲,仍住在緬因州。那天他幫曾祖父修剪樹枝,工作了一天之後非常地疲倦,坐在爐火邊睡著了。有人拍拍他的肩膀,他抬頭一看,看到主耶穌向他伸出兩隻手臂,手臂被鐵鍊所纏繞,「鐵鍊緊得陷入祂的骨肉裡」,他滿懷悲傷地告訴我,僅存的一隻好眼睛流露出舊日的哀痛,他說他當時就知道,日後他必須到堪薩斯州投身廢除奴隸的行列。老人家都希望自己能派上用場,最害怕成天漫無目標,我非常贊同這個觀點。我跟父親提到祖父所描述的異象,父親聽了僅是點點頭說:「那是時代的因素。」他自己從來沒有類似的經驗,他似乎也想跟我保證,有朝一日主若對我展現祂的哀愁,我無須感到害怕,我聽了放心多了,想來也覺得神奇。
在我眼中,祖父又老又病,事實上也是如此,他像是一個老被雷電打到的人,衣衫襤褸,頭髮永遠亂七八糟,醒著的時候一隻眼睛流露出哀傷與警戒。除了他的一些朋友之外,他是我見過最不安分的人,這些老人家即使上了年紀也寧願蹲坐著,好像跟桌椅有仇似的。他們瘦得只剩下一把骨頭,彷彿是群不情不願退休了的猶太先知,或是依然等著審判天使的老牧師。其中有個老先生,他替人祈福和施洗的那隻手上有個螺旋狀的烙印,據說他曾一把捉住一個小游擊隊員的槍身,所以手上才留下這個烙印。「我想那個小孩子不會開槍射我,」老人家說,「他還不到長鬍子的年紀,應該跟他母親待在家裡,所以我說:『你把那個東西給我。』他輕蔑地一笑,然後把槍遞過來,我只好接下,不然豈不讓他看笑話?我另一隻手臂綁了繃帶,無法接槍,所以只好用這隻手硬生生地把槍接下來、帶著槍走開。」
他們曾造訪蘭恩和奧伯林,通曉希伯來和希臘文,也讀過洛克和密爾頓的著作,有些人甚至在塔波鎮(Tabor)創辦了一所不錯的小型學院,學院運作了好些年,畢業生們特別是年輕的女孩,隻身前往地球另一端傳教或教書。他們在多年之後返回家鄉,跟大家分享在土耳其和韓國的見聞。但他們仍是一群魯莽的老傢伙,全都是一個樣,也難怪祖父的墳看起來好像有被放過火的痕跡。
我剛才聽著收音機播放的一首歌,聽著聽著,不禁站起來隨著旋律稍微搖擺,你母親可能從走廊上看到我,所以笑著對我說:「讓我示範一下吧。」她走過來、伸出手臂圈住我,把頭倚在我的肩膀上,過了一會兒,她用你所能想像的最輕柔口氣對我說:「你為什麼非得這麼老呢?」
我也同樣自問。
--------------------------
幾天之前,你和你母親帶著花回家。我知道你們上哪裡去,她當然帶你去那裡,讓你熟悉一下那個地方。我也聽到她把那個地方描述得很美,她真是個細心的女人。你拿了忍冬花教我怎麼吸出花蜜,你咬掉花朵的小小尖端,然後把它遞給我,我假裝不知道該拿它怎麼辦,我把整朵花放進嘴裡,假裝嚼一嚼吞下去,或是把花當作哨子,對著它吹氣,你邊笑邊說:不對!不對!不對!我又假裝有隻蜜蜂在我嘴裡飛舞,你說:「不,你嘴裡沒東西,根本沒有蜜蜂!」我一把捉住你的肩膀,對著你的耳朵吹氣,你猛然跳起來,好像真的看見一隻蜜蜂,然後捧腹大笑。過了一會兒,你嚴肅地對我說:「我要你這麼做。」說完就把手放在我的臉上、輕柔而小心地碰碰我嘴邊的花朵說:「好,吸一口。」你又說:「你吃藥的時間到了。」我依言照辦,藥的味道和忍冬花蜜一模一樣,恰似我在你這個年紀所嚐到的忍冬,那時每道籬笆旁邊、每個門廊欄杆之上,似乎都長滿了忍冬花。
那天下午的光線令我相當驚訝,我向來非常注意光線,但沒有人能充分領會光線之美。光線似乎帶有重量,擠出了草地上的水氣,逼出了門廊地板上的霉味,甚至有如晚冬的殘雪似地積壓著樹梢。光線駐足你的肩頭,彷若小貓窩在你的大腿上,感覺親切而熟悉。「小滑頭」躺在路邊曬太陽,你會記得「小滑頭」吧?說真的,我不知道你怎麼會記得牠?牠畢竟是一隻非常平常的貓咪。我會幫牠拍幾張照片。
我們就這麼吸吮著忍冬花的蜜汁,直到吃晚飯為止。你母親拿出照相機,說不定你以後會有些照片。我還沒來得及幫她拍照,底片就用完了,每次都是如此。有時我想幫她拍幾張照片,她不是把臉埋在雙手中,就是跑出房間。她認為自己不漂亮,我不曉得她為什麼覺得如此,我永遠也猜不透。有時候我不知道像她這麼一個年輕貌美的女子,為什麼會嫁給我這麼一個老人?我從沒想過跟她求婚,也絕對沒有這種勇氣。結婚是她提起的,我經常提醒自己,她也經常提醒我。
以前我絕不相信,有朝一日我會看著自己的妻子打點我們的孩子,現在每思及此,依然感到難以置信。我之所以寫這封信,部分原因在於未來你若懷疑自己究竟有何成就(每個人遲早都會有此疑問),請你記得,你是神給我的恩賜,
是一個比奇蹟更珍貴的奇蹟。你或許不太記得我,或許也不覺得身為一個小鎮老牧師的獨生子有什麼了不起,而你將來必然也會離開這殘破的小鎮。唉,我若能讓你明瞭就好囉!
孩童的頭髮在陽光下閃爍著光芒,彷若有時在朝露中看見的微小七彩光束,花朵的瓣片和孩童的皮膚上也泛著同樣的光芒。你的頭髮又直又黑,膚色非常白皙,你不比其他小孩漂亮,只是一個長得不錯的小男孩,個子雖然小了點,但乾乾淨淨很有禮貌。這些都無所謂,只因你活在世上,我就鍾愛著你。對目前的我而言,活著似乎是最不可思議之事,我即將邁向永生,可能就在剎那之間、眨眼之際。
眼中的星光,這是最奇妙的表達了。我經常心想,生命中最神奇的事莫過於此,人們一看萬物迷人之處或是領會到其中之妙,眼中就會綻放出耀眼的欣喜。「眼有光使心喜樂」(〈箴言〉第十五章第三十節),這話完全正確。
你讀到這封信時,我已置身於永生,說不定已恢復年輕時的活力,比以往更加生氣蓬勃,身旁也有心愛的人相伴。你讀到一個焦慮、糊塗老人的囈語,我卻生活在比夢境更美好的光明中;但我不等你,因為我希望你這副終將腐朽的軀體活得長長久久,好好享受這個終將腐朽的世界。即使我一直希望與露易莎和蘿貝卡再度聚首,但我真的無法想像怎能不思念這個世界。多年以來,我一直想像跟她們相逢之後將會如何。唉,我這個老種子即將歸於塵土,然後我就曉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