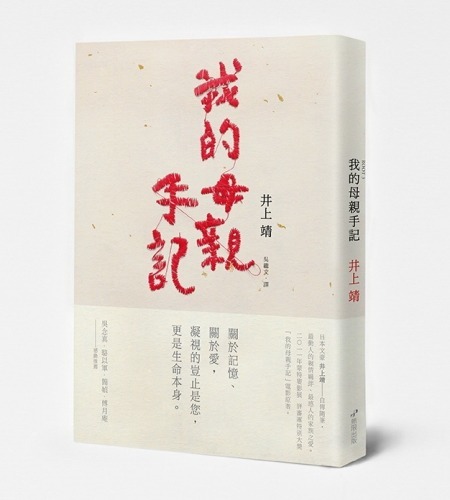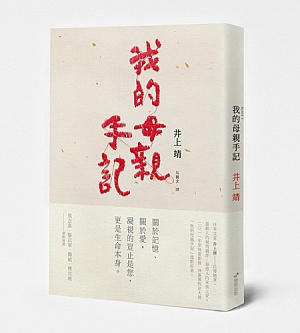•譯後記
冷靜的凝視
——吳繼文
友人的母親個性彆扭,和親戚、朋友幾乎都斷了往來,只有和她南部老家高齡九十的媽媽還算常聯絡,也不時寄些老人家愛吃的東西過去,聊表愛心。一天她竟也接獲老媽媽從高雄宅配來的各色食品,裏面還夾帶了一張以顫抖筆跡寫滿的關於如何保存、烹煮、食用的註記,突然驚呼連連:「天啊,我不知道她會寫字耶!」
並非不在乎,卻愛得漫不經心。
井上靖自言,這本由成立於三個時期的三篇文字合輯起來的書,既不能說是小說,也不算隨筆;換個說法就是,這部作品既有小說的虛構,也有隨筆的寫真。對瞭解他的讀者而言,以他成長史為藍本的著名三部曲《雪蟲》、《夏草冬濤》、《北之海》如果比較靠近小說那一端,而自敘傳《童年憶往》、《青春放浪》、《我的形成史》在紀實這一端,那麼本書正好介於其間。
父親由於職業(軍醫)的關係,每兩三年就必須調任一次,北至北海道,南到台灣;大概不希望他頻繁轉學吧,井上靖自懂事起就和原生家庭分居兩地,被安置在伊豆山區老家,和一個沒有血緣關係的初老女子佳乃,住在一棟老朽的土角庫房,相依為命。佳乃是井上靖非直系血親的曾祖父井上潔所納的妾,沒有正式名分,被鄉里家族排斥、敵視,正好和天涯孤獨的井上靖成為忘年的盟友。曾祖父死前對佳乃做了安排,讓她當井上靖母親八重的養母,另立門戶。陰差陽錯,這個輩分上算是井上靖曾祖母、戶籍上則是他祖母的外姓女子,竟然成為現在井上靖家系的第一祖,長眠於家族墓園。
伊豆半島多山,交通不便(那時出趟遠門必須先搭兩個小時馬車,再坐一個多小時輕便車,才能抵達東海道鐵路幹線上的三島火車站),雖然離首都東京不過百來里路,卻完全是兩個國度。然而自然界的豐饒,民風之淳樸,四時節慶之繽紛繚亂,讓善感的井上少年在懵懂中建構了屬於自己的世界,以抵抗無來由的孤獨與哀傷。父母家人總在遠方,他生命中關於家的最早印記,就是佳乃和老庫房。對他而言,奉獻式地照料他、溺愛他的佳乃,才是他的母親,甚至是情人;所有對佳乃不好、說佳乃壞話的,一律視之為敵人。這種同盟關係教人聯想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卡內提 (Elias Canetti) 和他的母親,只不過發生在歐洲猶太殷商家族的故事更多了知性的啓蒙 (《得救的舌頭》)。
父親隼雄帶著井上靖除外的其他家人,半生漂浪於日本列島、朝鮮、台灣之間,卻在五十壯盛之年退職還鄉,之後即隱遁不出,靠微薄的退休俸過著清簡的日子,不與外界往來,形同自閉;本來外向的母親卻也認命地隨自己丈夫在伊豆山野務農度日。然而這時井上靖早已成年,先是在京都大學就讀,接著是結婚、小說徵文獲獎、進報社工作、成為職業作家,除了偶爾歸省,還是和父母的生活沒有交集,簡單說就是一個和父母無緣的孩子。他知道父母並非不愛他這個長子,而他對自己的父母也一直有著複雜的情感,但也就是這樣。直到父親去世,母親日漸衰老,井上靖才突然驚覺,他並不真的瞭解父親(但已無從瞭解),而他同樣陌生的母親,則因為老年癡呆以致過往人生的記憶開始整片整片的剝落。再如何努力撿拾殘缺碎片,想要拼湊母親生命的完整圖像,為時已晚。時間的黑洞吞噬了一切。你對深淵呐喊,只能捕捉疑似的回聲。仿佛再度被母親所拋棄。
在寫於同一時期的《童年憶往》中,作者自言,當他追想幼年時光,幾乎沒有母親單獨出現的畫面,即使到青少年時代亦然。母親爲了他能夠順利考上中學,發願茹素,從此一生不沾葷辛,這麼重大的事件,他完全不記得。如果是爲了重建記憶,像奧地利劇作家、卡夫卡獎得主彼得•韓德克 (Peter Handke) 在母親於五十一歲那年突然仰藥自盡後所做的那樣 (《夢外之悲》),這本書將註定是一場徒然。
早年的井上靖,非常刻意地讓自己不要變成父親、母親那樣,過著無欲、退縮、冷清的人生。他不喜歡過去打麻將、玩撞球、下圍碁和將棋的父親,於是自己一輩子都不碰這些休閒遊戲。他擁抱人群,總是成為朋友聚會時歡笑的核心。家族代代行醫,所有人都覺得做為醫生長子的他理所當然要進醫學院,學成後繼承家業,結果他卻選擇了父親最瞧不起的哲學科主修美學。然而年過六十的他不得不承認,自己那猶疑不決、誰都不得罪的個性,簡直和父親一模一樣,而強烈的自我中心以及易感愛哭的德性,根本來自母親。多年以來,他讓自己成為這樣一個人:同時繼承了父親和母親的特性,卻強迫自己走一條和他們完全不一樣的路。從這個角度看,他成功了。可當他意識到,通過這些長期的、持續的對峙,他反而成了或許是世界上最能夠理解父母一生的人,可是他卻讓父母帶著不被理解的憮然,無限孤獨地離去。做為人子至親,他又是失敗的。尤其當他痛切體認到,正因為性格的雷同,父母不也才是他最佳的理解者嗎?然而父親已遠,母親不久亦將關上最後一道門窗。這是多麼尷尬的挫敗啊。
晚年的母親,沒有什麽病痛,卻明顯老衰,身形不斷萎縮,變成輕如枯葉的一縷幽魂,「從此以往再無任何可能性的肉身已經來到了它的終點」,而嚴重的失憶,讓她從倫常、責任甚至命運的重壓中脫身,孤立於塵世之上,對人世間的愛別離苦已不再關心,而他人亦無從探入她此刻的內心世界。仿佛抵達太陽系邊緣的星船,無法接收或傳送任何可辨識的訊號。她成了永恆的神秘本身。
在此,一個小說家能做的,就是直面凝視生命那壯絕的神秘。物自身 (das Ding an sich) 儘管不可知,但你依然可以思索,試著對話、發問,並加以描繪,捕捉如幻的現象,呈現可能的真實。這一切作為,都是對德爾斐 (Delphi) 神諭——認識你自己——的回應。井上靖的凝視,絕非徒然。準此而言,我們可不可以說,所有的小說,或多或少,都是「私小說」?
「私小說」不只是曝露或自我揭露。誰沒有秘密?你的命運與我何干?昭和文豪井上靖以此作向我們雄辯地演示了,唯有以冷靜的凝視之眼,揭開「不可知」的封印,穿過遺忘的荒煙蔓草,直探生之秘境,才是「私小說」的神髓。
然而更讓人掩卷低迴的是,這個以纖細的感性從事懷舊、悼亡的作者,言笑晏晏恍如昨日,如今也早已移身他界,成為不歸之人久矣。很快的,此刻做為觀看者、聆聽者的我們,不就像執筆當下的作者一樣,坐在一班正開始加速的時間列車上,而前方已經隱約浮現終站的燈火。
倒數計時,準備下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