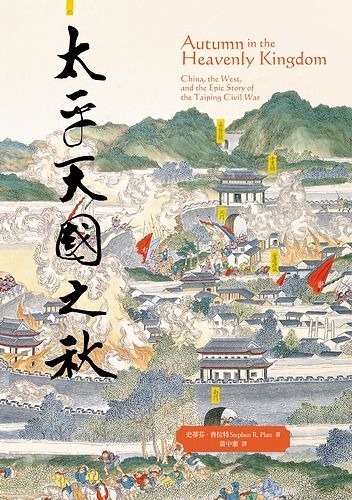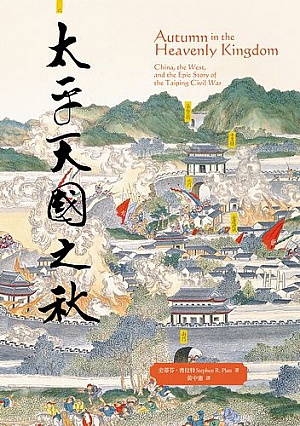前言:天子
一八五三年某個初春早上,北京正西北邊,太陽靜靜升到圓明園上方。這時當家的皇帝是咸豐,清朝第七個皇帝。圓明園占地遼闊,花木扶疏,由八百畝園林和精心建造的殿宇亭閣組成,成為中國世界中的世界。咸豐帝,一如其歷代先皇,鮮少需要出到圓明園之外。圓明園裡有木造的馳道、湖與戲樓。帝國內最壯麗的風景,化為小巧的假山假水,精巧重現於圓明園裡,供皇帝欣賞。二十一歲的咸豐登基才三年,但他就出生於圓明園,他這輩子唯一確知的事,就是準備成為天子,治理中國。
咸豐是滿人,不是漢人。他的先祖原居於長城以北,以游牧狩獵為生。更早的中國王朝建造長城,以將他這樣的民族拒於門外(漢人稱他們是蠻夷)。但一六四四年明朝遭滿人消滅後,他的家族統治中國至今已兩百多年,他們的統治手法頗為寬容,扮演中國傳統文化的管家,讓肩負實際管理與行政工作的漢族文人不致生出異心。一如過去的中國王朝,他們以科舉取士,吸收忠貞漢人替他們治理帝國。而這時,經過好幾代之後,已少有人質疑滿人統治是否天命所歸,滿人皇帝是否是上天選派來統治中國的人。
咸豐過著只他一人獨有的生活——全天下只有皇帝能穿黃色衣服,只有皇帝能用朱砂墨,只有皇帝能以朕自稱。從某個角度來看,帝國內更廣大地區的滿人也過著特權生活。他們是人數甚少的菁英(征服中國時滿人與漢人的比例是三比一千),有自己的語言和習俗,只跟自己族人通婚。一如深居宮中的咸豐,大部分滿人住在專為他們而闢的幾個城裡,也就是所謂的滿城。滿城位在築有城門的更大城市裡面,本身也有城門,以環城的高牆將自己與城外廣大的漢人隔開。
過去,滿人凶猛驃悍,每到夏天滿人男子會回北方的祖居地,練習使他們得以讓定居生活的漢人臣服的騎射之術。但隨著習於安逸,情況跟著改變。皇帝不再像過去的皇帝那樣關注外界的變化,滿族男人不再那麼熱衷於訓練體能、精進武藝。於是,一八五三年這個春天早上,當叛軍——另一個天命所歸者——衝破咸豐皇宮南邊一千一百多公里外的南京城外廓,大聲叫城民帶路找滿妖時,當叛軍推進到更裡面的滿城邊,一個個爬上將滿城李的居民與外界隔開的城牆時,住在滿城內兩萬左右的滿人並未拿起武器抵抗,反倒猛然趴下求饒。叛軍像宰畜牲般殺了他們,然後殺掉他們的妻子,還有他們的兒女。
第一章傳教士助理
一八五二年的香港是個潮濕又疾病肆虐的地方,大清帝國南方海岸外的多岩島嶼。有人說島上「到處開挖土地釋出瘴氣」,島上居民終日害怕瘴氣纏身。山與海灣之間座落著小小的英國人聚落,但翠綠與湛藍的山海風光使人看不到表象底下的陰暗。殖民地的主要街道,街名散發思鄉情緒(皇后大道、威靈頓街、荷里活道),貨棧、兵營、商行緊挨著矗立在主要街道上。離開這些建築,走上從海岸通往山丘的石子路,能看到最壯麗的景致,但走不久即離開白人聚落,觸目所見是散落於水稻田和甘薯田之間的華人房舍。自十年前英國人靠著鴉片戰爭拿到這座島嶼當戰利品之後,這一農村景致一直沒變。有些較有錢的商人在那些山丘上蓋了豪宅,宅邸中呈階梯狀布局的花園將山下的港灣和城區盡收眼底。但這些大宅的主人好似離開殖民地的保護圈太遠,宅中居民於是生病,然後死亡。這些陰森森的宅邸被冠上「熱病屋或死人屋」之名,靜悄悄座落在山間,人去樓空,其空洞的眼神向山下的移民發出冷冷的批判。
韓山文(Theodore Hamberg)是那些移民之一。他是瑞典籍的年輕傳教士,薄薄的落腮鬍襯出他秀氣、幾乎女孩子氣的五官。他天生有著迷人的嗓音,年輕時在斯德哥爾摩曾與「瑞典夜鶯」珍妮.林德(Jenny Lind)同臺合唱。但林德繼續走歌唱之路,風靡歐美歌劇院,令蕭邦與安徒生之類仰慕者拜倒在她石榴裙下時,韓山文的人生有了一百八十度的轉折。他雄渾有力的男高音,在講道壇上找到注定的發揮舞臺,一八四七年離開故鄉瑞典,坐船來到地球另一端,瘧疾橫行的香港殖民地,心裡只想著要以另一種方式讓中國人臣服。
韓山文本來大有可能沒沒無聞度過一生,因為他最自豪的成就,在小小的新教傳教士圈子以外沒人看在眼裡。他是他那一代最早勇闖中國鄉間的歐洲人之一。他離開較安全的香港,到中國商港廣州之外,珠江更上游一百六十公里處的一個村子傳教(但後來基於健康考量,他還是回到香港殖民地)。他也是第一個學會客家話的歐洲人。客家人是吉普賽似的少數族群,在華南人數頗多。若非一八五二年晚春某日,有位因他而皈依天主的鄉下人帶了一個客人來找他,他這一切努力大概得不到世人多大重視。那是個矮小圓臉的客家人,名叫洪仁玕,有著一段精采的人生經歷要說。
韓山文憶起他們第一次見面的情景,說這個客家人最讓他奇怪的地方,是他似乎已非常瞭解上帝和耶穌,儘管他來自的地方離香港傳教士狹小的活動範圍很遠。韓山文帶著好奇,聽洪仁玕講述使他踏上香港的眾多機緣,聽得一頭霧水。他說到異夢和戰鬥,說到由信徒組成的軍隊和禮拜會,說到一名客家人出身的先知。他被清朝特務追捕,易名到處躲藏,至少他是這麼說。他曾遭綁架,然後逃脫,曾在森林裡住了四天,在山洞裡住了六天。但這一切聽來太光怪陸離,韓山文坦承:「我搞不清楚這是怎麼回事。」他不知道洪仁玕說這些遭遇的用意,於是請洪仁玕寫下來,洪仁玕照做,然後——韓山文原以為他會留下來受洗——沒說什麼就離去。韓山文把洪仁玕寫下自身遭遇的那疊紙放進書桌抽屜,將心思擺在其他事情上。此後將近一年,他沒把這些紙放在心上,直到一八五三年春得知南京已倒在鮮血洪流中,韓山文才意會到洪仁玕粗略交待的那些怪事,意義超乎他想像。
* * *
韓山文跟香港及上海的其他移民,完全是透過零星含糊的傳聞,得知中國境內情勢日益動盪。從中國的政府報告,似乎看不出一八五○年代初期日益升高的混亂有什麼模式,看不出存在什麼原則或協力行動之處。中國鄉間的地方暴亂和小股盜匪橫行,始終是帝國當局的困擾,談不上是新鮮事或值得一顧,儘管在鴉片戰爭後這幾年,這類事的確變多了。深入中國內陸的本國旅人和見不得光的天主教傳教士,說起他們聽到的傳言:有個更大的運動團體出現,那個團體由名叫「天德」的人領導。但許多傳聞說那人已經死在官兵手裡,或說根本沒那個人。在沒有明確消息下,沿海港口的洋人對這類事情不大關心,只擔心土匪使茶葉和絲的生產停擺。
但一八五三年南京城的陷落,把一場龐大內戰直推到上海租界的大門前。上海位於長江入海口,距更上游的南京只約三百公里。五十萬名自稱太平天國的叛軍,從華中搭乘大批徵來的船,浩浩蕩蕩湧向南京,所過之處,城市變成空城,政府防禦工事變成廢物。情勢非常清楚,這不只是土匪作亂。上海人心惶惶。與南京的直接通訊斷絕,情況渾沌不明(美國汽輪薩斯魁哈納號﹝Susquehanna﹞想溯江而上到南京查個清楚,結果擱淺在路上)。謠傳叛亂分子接下來會進軍上海攻打洋人,上海縣城裡的本國居民把門窗封死,收拾家具,搭上河船或逃到鄉間避難。洋人倉促著手防禦,臨時找來一批志願者組成防守隊守城牆,並備好幾艘船,打算情勢不妙就上船離開——兩艘英國汽輪和一艘雙桅橫帆戰船,還有供法國人與美國人搭乘的汽輪各一艘。
但太平軍到南京就停住,至少目前是如此。太平軍並未進軍上海,上海警戒解除。叛軍把矛頭朝北,指向滿清都城北京,以南京為作戰基地,掘壕固守,準備打一場漫長且慘烈的戰役。他們把南京改名「天京」,天京距上海不近又不遠,令上海洋人想一探究竟。一八五三年四月下旬,就有艘英國船排除萬難抵達南京,但帶回來的南京動態消息卻相互矛盾。最明確的看法出自英國全權代表之口,他宣稱太平天國擁有由「迷信與胡說八道」構成的意識形態。那些去過的人對叛軍的出身一無所悉。
儘管欠缺明確的訊息,有關中國內戰的第一手陳述還是從上海和香港往外傳,引起西方世界的注意。歐洲剛在五年前經歷過一八四八年革命的巨變,中國的動亂似乎與之有明顯的相似之處:悲慘的中國人民,遭滿人主子欺壓,如今終於挺身要求改變。《經濟學人》稱那是「與最近歐洲所遭遇者類似的社會變動或動亂」,說「亞、歐同時發生類似的騷亂,史上絕無僅有。」由此可見,地球另一端的帝國如今和西方的經濟及政治制度有了連結。
一八五三年擔任《紐約每日論壇報》倫敦通訊記者,正埋頭理清他對資本主義之看法的馬克思,也認為中國這場叛亂表示中國融入全球經濟,稱它是英國在最近的鴉片戰爭中強迫中國開港通商的最終結果。照馬克思的說法,中國所正發生的事,不只是叛亂或數場暴動的合流,而是「一場令人讚嘆的革命」,那革命表明工業世界的息息相關。他甚至主張,正是在中國,可以看到西方的未來:「歐洲人民的下一場暴動,他們爭取共和自由與管控政府的下一個作為,其成敗或許較可能取決於目前在天朝上國——與歐洲完全相反的國度——所發生的事,而較不可能取決於如今存在的其他任何政治大業。」
誠如他所說明的,中國這場動亂肇因於鴉片貿易;十年前英國用戰船強行打開中國的市場,從中削弱了中國人對其統治王朝的「盲目相信」。他深信,與外面世界接觸將摧毀舊秩序,因為「腐爛必然隨之發生,就像任何細心保存在密封棺材裡的木乃伊,一旦與室外空氣接觸,就必會腐爛一樣。」但受清朝腐爛影響者,不會只有中國自己。在他看來,整個太平革命是英國所造成,而英國海外作為的影響,如今將回傳到國內:他寫道,「不確定的是那場革命最終會如何反作用在英格蘭身上,且透過英格蘭反作用在歐洲身上。」
馬克思預測,中國市場落入太平革命團體之手,將削弱英國的棉花與羊毛出口。在動亂的中國,商人將只接受用金銀條塊換取他們的商品,從而使英國的貴金屬存量愈來愈少。更糟糕的是,這場革命將切斷英國的茶葉進口來源,大部分英國人所嗜飲的茶葉,在英格蘭的價格將暴漲,同時,西歐境內的農作物欠收看來很可能使糧價飆漲,從而進一步降低對製成品的需求,削弱英國經濟所倚賴的整個製造業。最後,馬克思斷言,「或許可以篤定的說,這場中國革命會將火星擲入現今工業體系已然過載的礦場,使醞釀已久的大危機爆開,然後在往國外擴散之後,緊接著歐陸會爆發政治革命。」
如果說馬克思一心想讓《紐約每日論壇報》的讀者相信,這場中國內戰是與歐洲境內的運動類似的階級鬥爭和經濟革命運動,那麼美國南方奴隸港紐奧良的《每日一銅幣報》(Daily Picayune)的主編則從他們自身的世界觀出發,以大不相同的角度看待這件事。誠如這些主編所認為,這是場種族戰爭,中國是劇變中的奴隸國。他們解釋道,太平軍發跡於廣西和廣東這兩個南部省分,兩省居民「基本上是中國原始種族」。相對的,北方的滿人是「中國的統治種族」,自兩百年前入主中國之後,「中國一直被其主子當成受征服國家來統治」。他們解釋道,兩個種族從未混合,然後,與他們的美國南方觀點——以奴隸為基礎的和諧社會觀——相一致的,該報表示,在中國,「不多言、有耐心、刻苦的數百萬人,以足堪表率的溫柔敦厚,接受他們主子的統治。」這個主奴和平共處的滿漢國,唯一威脅其穩定者是這些不願接受宰制的華南「原始」人。於是,太平叛亂與美國黑奴的暴動,有了令人神傷的相似之處。
倫敦《泰晤士報》最有先見之明,立即抓住問題核心,探討英國是否該派海軍投入這場中國內戰,以及如果這麼做,該站在哪一邊。在一八五三年五月十七日,也就是南京陷落的消息傳到倫敦後不久,《泰晤士報》某篇社論指出,太平天國似乎所向披靡,「據各種可計算的機率,他們會推翻中國政府。」《泰晤士報》還轉載了上海某報的一篇報導,問道「換人當家作主」是否是大部分中國人所想要,並表示太平天國雖然在華北不大受喜愛,卻代表了一股漢人所樂見的改變力量,「認為不該再忍受官員橫徵暴斂和壓迫的心態,似乎在全國各地都愈來愈濃。」到了夏末,《泰晤士報》直截了當宣告,中國這場叛亂「就各方面來看,都是世人所見過最大的革命」。
但叛軍本身卻是個謎。《泰晤士報》讀者會輕易斷言,太平天國得到漢人的支持——至少得到勉強的支持——準備推翻滿人,開啟新政。但該報主編也就英國的無知發出告誡之意。「關於叛亂的源起或目標,我們沒有具體的訊息,」他們寫道。「我們知道現在的中國政府可能在內戰中遭推翻,但就只知道如此。」他們憂心英國不夠瞭解叛軍的本質或意識形態,而無法決定該不該予以支持或鼓勵:「在這件事情上,我們無法斷定我們的利益或職責該落在哪一邊——這場叛亂有正當理由或無正當理由,前途看好或不看好;民心向背如何,或它的成功會促成我們與中國人的關係往好或往壞的方向改變,或是否會促成改變。」但事實表明,其中最迫切的問題——叛亂的根源、太平天國是什麼樣的組織、他們的信念為何——答案將在香港尋得。答案就潦草寫在幾張紙上,而那些紙就塞在韓山文書桌的抽屜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