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者:許瑞宋
出版品牌:衛城出版
出版日期:2023-06-28
產品編號:978626705285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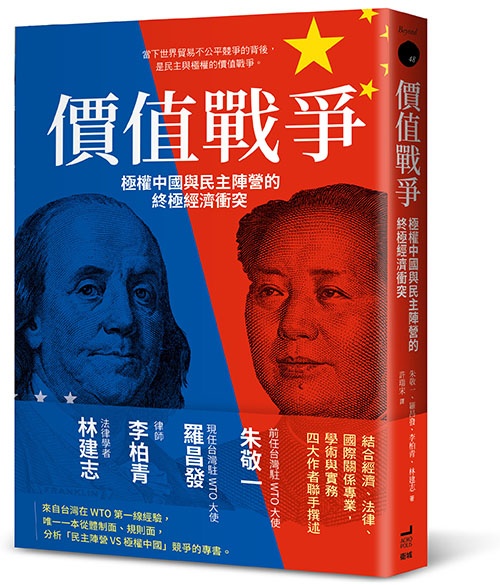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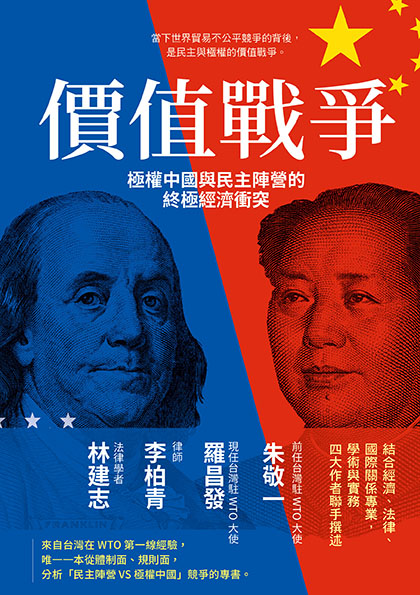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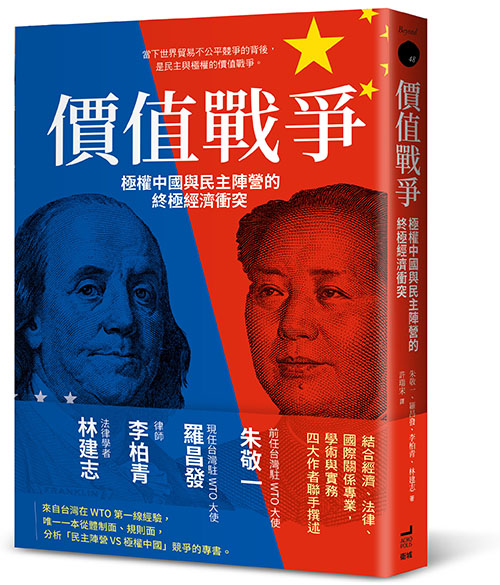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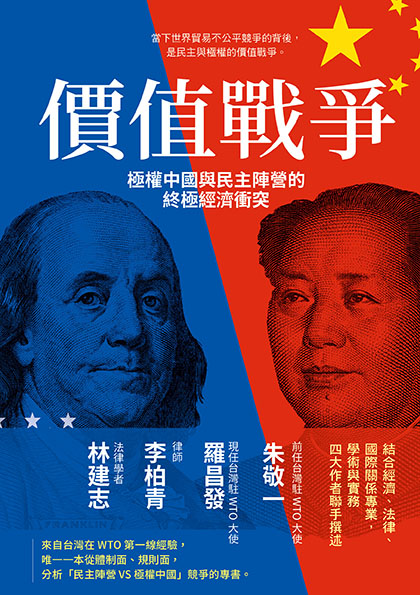
全面解讀:
民主陣營VS極權中國,無法避免的衝突根源
極權中國進入世界貿易體系後,
為何令世貿規則漏洞頻出?
未來能如何修補?
來自台灣在WTO第一線經驗,
唯一一本從體制面、規則面,
分析「民主陣營 VS 極權中國」競爭的專書。
當西方與共產陣營的冷戰結束時,世界彷彿迎來民主政治與自由經濟的勝利時刻,國際社會開始積極建立合作關係。1995年,世界貿易組織(WTO)成立。2001年,中國加入WTO。樂觀者謳歌著世界是平坦的,彷彿一體的國際經貿體系已經誕生。
然而,二十年後的今天,問題浮現。極權中國加入WTO二十年,其與民主陣營截然不同的價值觀點,對世界貿易規則產生扭曲效應。世界不但沒有走向和平共榮,反而再次深陷極權與民主兩大陣營的衝突。
這一次,「民主陣營 VS 極權中國」,在全球連結、網絡科技的環境中交手。雙方價值上的差異,牽一髮而動全身,多年來已經產生隱性的競爭不公,也埋下衝突的種子。
過往談論國際關係,往往從「利益」出發。然而在當下中國與民主陣營的經濟衝突中,「利益」與「價值」無法截然區分。中國企業的競爭力,來自背後黨與國家力量的支持。這樣的黨國經濟制度,與民主國家強調的制衡、機會均等、公平競爭相互矛盾。因此雙方的貿易競爭,最後必然會連結到民主與極權價值之爭……
本書四大作者,結合法學、國際貿易、經濟領域專業,兼具學術與實務,且從台灣在WTO現場的寶貴經驗出發,分析WTO過往規則上的漏洞,也描繪出重整規則的新可能。民主陣營既要保護民主價值,又要警覺、務實地與極權國家互動,唯有從規則面著手—
「無論幸或不幸,我們有機會身處世界貿易組織(WTO)的前線,觀察到WTO組織氣氛的劇變,見到WTO解決爭端的制度如何癱瘓,也目睹WTO的成員在這場貿易戰期間何其沮喪。這種獨特的『戰爭前線』觀察成為我們寫這本書的第一個動機,因為我們希望研究、並找出世上最大的兩個國家爆發如此巨大衝突的體制面原因。」—本書作者
本書特色
推薦記錄
為何中國與民主國家間的經濟衝突終究無法避免?全球經貿規則需要如何調整,以改革現行WTO體制之不足?《價值戰爭:極權中國與民主陣營的終極經濟衝突》提供了我們真知灼見的分析,也帶來豐富多樣的實證案例,紮實地證明了國際經貿交流也無法自外於威權政治的負面影響,是以「台灣觀點」貢獻國際討論的絕佳典範。
—鄭麗君,青平台基金會董事長
作者以嚴謹學術論述與親身實務觀察,剖析美中經貿衝突根植於民主與專制價值差異對公平競爭與經濟利益的影響。要瞭解美中經貿衝突核心問題的人,都應該詳加研讀本書。
—蘇建榮,國立臺北大學財政學系教授、財團法人台灣金融研訓院董事長
這本書告訴我們,什麼叫做「創意」。有關民主體制的比較研究,國內外的討論與出版品,已是汗牛充棟。但是從現代科技(5 G)、普及的數位交易,再加上實証的調查等等,這本書為民主體制的比較研究,開啓嶄新的另一扇門。
—邱義仁,新境界文教基金會副董事長
數位極權對內壓制、對外擴張,嚴重威脅全球政經秩序。本書從科技、經貿、制度觀點提出分析建議,為民主夥伴奠定堅實基礎。
—唐鳳
不同於美蘇冷戰的壁壘分明,美中之間千絲萬縷的經濟衝突,本書結合經濟與法學觀點,提供了有力的論點。
—沈榮欽,加拿大約克大學副教授
獨裁者主導的國家資本主義如何發生?有什麼特徵?跟我們的民主價值會產生什麼衝突?最重要的,我們又該如何面對?四位作者長期在這場無煙硝的戰役最前線折衝,精闢的分析對台灣的未來是重要的參考。
—林明仁,台大經濟系特聘教授
有如師徒聯手的老少組合,面對國家價值抗衡與經濟利益競爭的混亂世局,透過實證論述解析為讀者敲山震虎,也為思考經貿困境的決策者指引迷津。
—張瑞昌,財團法人中央通訊社社長
朱敬一與他中研院同事們合寫的這本書,來得正是時候,這本書著眼於美中之間的經濟關係,從學術與實務的角度,對美中之間深刻的裂痕,提出了獨到的見解。與過去幾十年來許多政策制定者和學者的期望相反,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和其他多邊機構,並沒有使它在共同價值觀方面變得與美國及其盟友更為一致。中國在經濟繁榮之餘,反而為了中國政府的利益,試圖改變自由經濟秩序。這本書是重要的研究成果,架構清晰,證據有力,有助讀者認清這個事實:兩大超級強國之間的競爭,是不同的原則之爭,兩者之間的分歧勢必難以彌合。
─林夏如,美國維吉尼亞大學、香港中文大學、布魯金斯學會
這本書令人眼界大開,改變了我對中國與先進市場經濟體關係的看法。目前世界上有許多人面臨著兩難:既渴望進入中國這個成長中的巨大市場,又對進入中國市場將面臨的嚴重風險和挑戰憂心忡忡(他們的這種憂心是合理的)。我強烈推薦,想多了解這個兩難問題的人都應該要讀這本書。
─何漢理(Harry Harding),美國維吉尼亞大學
這本著作的到來恰逢其時,對市場經濟與國家資本主義之間的經濟衝突,尤其是美國與中國的經濟衝突,提出了獨到和深入的分析。本書的每一個主要章節,各探討一個在兩種體制間,因制度差異而產生的重大、根本的分歧。本書論述清晰,內容豐富,而且有實證支持。它有助讀者更深入理解當前美國與中國之間的經濟衝突,並指出在現行世貿組織規則和法律制度下解決這些衝突的困難。正如作者所言,本書的重點不在於探討哪一種體制比較好,而是希望釐清衝突的根源。只有明白衝突的真正源頭,我們才能找到克服衝突的方法。因此,我強烈推薦本書給所有商業和經濟的政策制訂者,以及所有關心美中關係的人。
─蔡瑞胸,美國芝加哥大學布斯商學院計量經濟學與統計學講座教授
在這本書中,朱敬一與合著者仔細研究了圍繞著中國獨特的國家資本主義制度各種懸而未決的問題,提出了豐富的論述。近年來,許多政策制定者在做決定的時候,把學術研究的發現晾在一旁,光靠直覺做決定,如此罔顧研究成果的政策制訂,無法保護自由經濟的利益。本書作者藉由全面重新審視經濟文獻,並且高度注意中國做法中最明顯違背市場期望的一些例子,為這個議題提出了新的見解,也扣合了時勢的最新發展。如今主要經濟體正在擺脫過去幾年資訊不足的單邊主義,開始認真合作,為不再假定所有國家終將奉行市場原則的新時代制定議程,這本書來得正是時候。
─榮大聶(Daniel Rosen),美國榮鼎集團(Rhodium Group)合夥人
台灣推薦陣容:
汪 浩_作家
沈榮欽_加拿大約克大學副教授
林明仁_臺大經濟系特聘教授
邱義仁_新境界文教基金會副董事長
唐鳳
梁永煌_《今周刊》發行人
鄭麗君_青平台董事長
蘇建榮_財團法人台灣金融研訓院董事長
李喜明_前參謀總長
林 全_臺灣東洋藥品董事長
吳介民_中研院社會所研究員
周奕成_專欄作家
張瑞昌_財團法人中央通訊社社長
童子賢_和碩聯合科技董事長
瞿筱葳_g0v零時政府共同發起人
國際推薦陣容:
孔傑榮_外交關係協會亞洲兼任高級研究員
林夏如_美國維吉尼亞大學、香港中文大學、布魯金斯學會
何漢理(Harry Harding)_中國問題專家、柯林頓總統特別國家安全顧問
蔡瑞胸_美國芝加哥大學布斯商學院計量經濟學與統計學講座教授
榮大聶(Daniel Rosen)_美國榮鼎集團(Rhodium Group)合夥人
朱敬一
美國密西根大學經濟學博士,中央研究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學院(TWAS)院士,美國國家科學院(NAS)海外院士。曾任中研院副院長、中華經濟研究院董事長、行政院政務委員、國家科學委員會主委、台灣駐世界貿易組織(WTO)常任代表等職。在學術研究之外,著有面向大眾讀者的《牧羊人讀書筆記》、《給青年知識追求者的十封信》、《朱敬一講社會科學:台灣社會的新世紀挑戰》、《經濟學的新視野》、《維尼、跳虎與台灣民主》等書。
羅昌發
哈佛大學法學博士。現任臺灣常駐世界貿易組織代表團常任代表。曾任中華民國司法院大法官、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院院長、臺大講座教授及特聘教授,為國際貿易法領域的權威。著有《國際貿易法》、Treaty Interpretation under the Vienna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reaties: A New Round of Codification等書。
李柏青
臺大法律系畢業,紐約大學法律碩士,曾任我國世界貿易組織(WTO)代表團法律顧問,現為貿易法方面執業律師;同時為臺灣推理作家協會會員,著有歷史作品《滅蜀記》、《亂世的揭幕者:董卓傳》,推理作品《親愛的你》、《婚前一年》等。
林建志
芝加哥大學法學博士,中央研究院法律學研究所副研究員,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副教授(合聘),研究領域為憲法、比較憲法、司法政治、司法行為。著有Constitutional Convergence in East Asia(與葉保仁合著,劍橋大學出版)。
許瑞宋
香港科技大學會計系畢業,曾任路透中文新聞部編譯、培訓編輯和責任編輯。2011年獲第一屆林語堂文學翻譯獎。譯有《貿易的取捨》、《不存在的金融革命》、《藥品帝國:從阿斯匹靈到COVID-19疫苗的人類醫藥壟斷史》等數十本書。
內文試閱
第一章 引言:當「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走向世界
美中衝突升級
二〇一七至二〇二〇年,在美國總統川普執政期間,國際關係上最重要的事件就是美國與中國的衝突升級。這當然不是歷史上美國第一次與其他國家發生貿易衝突;一九八〇年代的美日貿易衝突是美國與其他國家衝突的案例之一。不過,之前的美日貿易衝突與當下的美中貿易戰截然不同。以前者而言,雖然美國與日本在制度上有一些差異,但兩國的經濟決策仍大致遵循市場理性。中國所代表的社會主義經濟就不同了。因為在社會主義經濟體制中,「國家擁有生產手段,國家的規劃與官僚體系的目標設定,不是為了達成發展目標的理性手段……它們本身就是基本價值。我們不能拿低效率或無效率當作理由來質疑國家。」從這個角度看,美國與中國的衝突從最初關乎不公平貿易,迅速延伸至科技以至金融領域,也就不足為奇。曾任美國國家安全顧問的波頓認為,貿易問題只是冰山一角,美中之間的結構性問題才是導致美中衝突的真正因素(Bolton, 2020)。當然,這絕不僅是波頓個人的鷹派觀點;事實上,許多人也曾發表過類似的言論。在這一章中,我們會先概述上述的結構性問題和美中衝突的演變。至於更詳細的資訊,我們將在後面的章節提供,本章因此會先略過一些細節。
二〇一八年三月二十二日,川普政府開始對中國出口至美國的六百億美元商品課徵關稅。這個純粹的貿易措施很快就擴展至科技方面:二〇一八年四月十六日,美國宣布禁止美國企業出售零組件給中國電訊製造商中興通訊。然後在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一日,加拿大政府應美國司法部的要求,逮捕了中國主要電訊公司華為的副董事長暨財務長孟晚舟。美國指控華為將使用了美國零組件的產品出口至伊朗和北韓,違反了美國對這兩個國家的制裁。由於華為是中國第五代通訊(5G)發展的領導廠商,外界咸認為逮捕孟晚舟反映了美國對美中5G競爭的態度。
二〇二〇年八月六日,川普政府下令,在紐約證交所和納斯達克上市的一些公司必須接受美國的審計,否則必須在二〇二二年前下市。雖然這項行政命令沒有提到具體的公司名稱,但所有新聞報導都指出,當局的目標是與中國和香港有關的兩百八十三家上市公司。這是美中衝突第一次蔓延到金融層面。此外,在二〇二〇年,美國政府多次將更多中國公司列入實體清單,逐漸增加針對中國的制裁項目。
本書的目的是分析這場美中經濟衝突的各個面向。為了理解美中衝突發生的根本原因,我們審視了專制共產主義的中國,與民主資本主義國家如美國、日本、德國、英國和澳洲,在體制和意識形態上的差異。在本書中,我們以「市場經濟」和「黨國資本主義」分別指稱西方自由民主國家和中國的經濟模式。根據穆薩基奧與拉扎里尼的說法(Musacchio and Lazzarini, 2014),在國家資本主義體制中,「政府廣泛影響經濟,手段包括持有企業的多數或少數股權,以及向私營公司提供信用補貼或其他特權」。而在中國所代表的黨國資本主義下,政府背後同時有「國家」與「共產黨」雙重身影。相對之下,在市場經濟體制中,政府的角色較為有限,經濟決策主要是受供給和需求驅動和影響。我們明白,這兩種模式只是理念類型,也就是說,它們無法精確描述西方或中國的經濟行為屬於哪一類型;現實中有許多中間或混合模式,把這兩種理念類型的元素結合在一起。雖然有這樣的侷限,我們仍然認為這兩個概念雖然不精確,但作為本書的分析工具還是很有用。
當我們比較黨國資本主義與市場經濟背後的意識形態時,我們不把重點放在人們常提到的價值觀差異(例如自由或民主之類的價值問題),而是放在這種價值觀和體制差異導致的經濟層面影響。為了了解為什麼價值觀差異最終會導致終極經濟衝突,我們會先討論川普政府提出的一個廣為人知的批評:讓中國加入世貿組織是美國犯下的錯誤。說美國政府「犯了錯誤」是什麼意思呢?如果說,中國在經濟上的行為與美國和其他民主國家所期望的不同,那是為什麼?如果中國繼續維持現行政治體制,我們可以預測和預料將來還將有哪些經濟衝突?此外,最重要的是,這種預期衝突與專制共產主義與民主之間的體制差異有什麼關係?
經濟發展會促成民主嗎?
有關經濟發展與政治體制變革的關係,二十年前中國加入世貿組織時,當時主流觀點認為,將中國納入全球市場經濟體系,最終將會改變中國的政治體制,中國很可能就此走向民主,至少在某個程度上或在某些領域裡應該會如此「民主化」。但事實證明,中國辜負了這個期望:自加入世貿組織以來,中國濫用其超快速經濟成長所帶來的機會,積極推進它的獨裁目標。換句話說,問題不僅是中國沒有民主化,而是中國在取得經濟成就的同時,變得比以前更極權。前述「經濟發展促成民主」的主流觀點雖然現在看來完全是不切實際的一廂情願,但政治科學的研究文獻中的確有一些理論分析支持該觀點。接下來我們先回顧相關討論,然後再提出我們自己的看法。
民主與經濟發展之間的交互影響,是社會科學界長年以來討論的一個課題。李普賽是探討這個課題的先驅(Lipset, 1959),在他之後有戴雅門與林茲(Diamond and Linz, 1989)、英格哈特與威爾采(Inglehart and Welzel, 2010)、艾塞默魯與羅賓森(Acemoglu and Robinson, 2012, 2019),還有其他許多人。李普賽認為,經濟發展有可能促成民主,因為經濟發展會產生特定的社會文化變化,而這些變化會造成人類行為的改變(Lipset, 1959)。戴雅門與林茲則提出這種交互影響的三種可能方式(Diamond and Linz, 1989),以下逐一討論之。
首先,有一個論點是認為,經濟表現不佳很可能引起大眾的焦慮和不滿。焦慮日甚的社會氣氛通常歡迎強權領導,而這與民主的發展並不相容。因此,健康的經濟是民主永續的一個必要條件。但我們注意到:一、這個論點並不意味著經濟發展是民主的充分條件;二、這個論點關注的是民主永續的問題,而不是從專制政體轉向民主的轉變問題。
第二,研究人員發現,經濟發展往往伴隨著都市化、識字率提高、教育機會普及,以及與民主國家人民的社群互動變得比較密切。這些都有利於人權觀念和民主思想的推廣。但是,這個論點同樣只是觀察到經濟發展與一種有利於民主的社會環境之間的「相關性」,並不表示經濟發展與民主化之間有因果關係。
第三,我們觀察到,經濟發展有助於促進中產階級和相關社會組織的崛起,進而能夠對政府的施政施加壓力並且予以制衡;這種制衡與民主化的發展當然是一致的。但這個論點也同樣不嚴謹:中產階級崛起推動政權走向民主只是一種設想,是否真的發生難以確定,因為有很多因素可能導致政權往其他方向演變。
綜上所述,上述論點為民主與經濟發展的相關性提供了概念上的支持,但並不構成嚴謹的因果論證。英格哈特和威爾采等研究者就已經提出了經濟發展並沒有促成民主的許多實際案例(Inglehart and Welzel, 2010)。而即使有大規模跨國調查的資料可供分析,學術界還是未能確立經濟成功促成民主的因果關係。此外,由於政治體制變革速度緩慢,研究者很難觀察到政治體制穩定過程的全貌,也很難基於有限的觀察得出嚴謹的推論。最後,新加坡的例子反映了一個灰色地帶:該國既不民主也不完全專制,但半個世紀以來,它是世界上經濟成長最快的國家之一。
過去三十年間,最令人不安的例子當然是中國。一九九〇至二〇二〇年間,中國經歷了空前快速的經濟成長,三十年間國內生產毛額(GDP)增加了約四十倍。中國傾向將其經濟成就解釋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或「具有社會主義特色的市場經濟」)的典範。姑且不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確切含義如何,如果這個典範論成立,它顯然駁倒了經濟發展會促成政治民主的說法。無論以什麼標準衡量,二〇二一年的中國可能是世界上最專制的國家之一。
那麼,如果經濟發展會促成政治自由化的預測不成立,專制國家的下一步將會如何?在這個全球化已經不可逆轉的時代,世界要如何應對兩種經濟體制──一種是民主的市場經濟,另一種是以中國(或許還有俄羅斯)為代表的專制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我們是否應該期待看到,將有一種世界經濟秩序以某種方式調和這兩種體制呢?抑或,這兩種體制之間存在根本的制度差異,而這意味著未來的衝突無可避免呢?本書將試著回答這些問題。
中國企業在世界經濟中的奇特角色
中國經濟成功的故事也與本章開頭提到的美中衝突有關。美國貿易代表署在多份WTO文件中表示,中國的經濟成就(至少某程度上)靠的是各種不光彩的手段,包括強迫技術移轉、盜竊智慧財產權、政府大量補貼、操縱匯率,以及違反現行WTO規則或鑽漏洞等許許多多其他手段。根據朱敬一與李柏青的研究(Chu and Lee, 2019),美國的指控有一定的道理,因為一九九四年簽訂的《馬拉喀什協定》(Marrakech Agreement,此為WTO成立的法律基礎)確實存在漏洞。今天的世界與一九九四年時已經大不相同,而中國確實利用了很早以前制定的WTO舊規則來佔其他國家便宜。
朱敬一與李柏青指出了現在與《馬拉喀什協定》制定時的三項環境差異(Chu and Lee, 2019)。在這裡,我們僅簡述其中兩項,細節留待後面的章節闡述。現在的情況與一九九四年的第一項差異,是知識經濟的崛起。在一九九四年,半導體的摩爾定律還只是一個猜想;人類基因組計畫還沒開始;基於研發的高科技產業和創投公司尚未興起,今天的許多高科技巨頭當時甚至還沒冒出頭。一九九四年頒布的《關稅暨貿易總協定》(GATT),其規則主要涉及傳統產業。為了在這些傳統產業維持公平的國際競爭,貿易規則主要規管介於「工廠」與「市場」之間的政府補貼。但在高科技產業,一種新的、可能更重要的補貼出現了,那就是從「研發實驗室」到「工廠」的補貼。中國政府在這個早期階段就提供了許多補貼,但現行WTO規則無法有效規管這些補貼。簡言之,《關稅暨貿易總協定》管制的補貼針對「已經存在」的商品,但高科技產業的補貼卻是針對「還不存在」的商品,希望靠補貼促成其商品之出現。
一九九四年沒有預料到的第二種情況,則與蘇聯和中國快速市場化有關。蘇聯一九九一年開始解體,鄧小平則是在一九九二年發表南巡講話,進而全面啟動中國的市場化。各國起草《馬拉喀什協議》時,是基於正統的西方市場經濟背景,假定企業與政府是不同的實體。但中國的情況完全不是這樣。
在中國,以前完全由政府或中國共產黨擁有的企業迅速私有化,創造出很大比例的偽私營企業;擁有或控制這些私營企業的人,多數與政府或黨高層有良好關係。這種怪異的經濟狀況可稱為黨國權貴資本主義(state-party crony capitalism)。因此,在中國(或許還有俄羅斯),企業與政府在其體制設計和關鍵人員方面,兩者之間實際上有剪不斷的關連。
馬利德(McGregor)指出,在決策方面,中國沒有真正的「私營」企業;該國所有企業,尤其是大型企業,皆受中國共產黨嚴格控制(McGregor, 2010)。他引用其他人的觀點,得出中國GDP僅二〇%至三〇%是由真正私營企業貢獻的結論(p. 199)。許多中國大公司的執行長辦公室裡有個「紅色電話」,連接中共內部的通訊線路,方便共產黨在必要時向執行長發出關於業務方向的指示(p. 29)。多數公司並不厭惡這個紅色電話,反而視之為公司與黨關係密切的象徵,而這種關係可在關鍵時刻提供公司營運上的便利。
馬利德指出,雖然法律沒有明文規定,但中國共產黨可以針對公司的政策發出指示,決定公司董事會成員和執行長的人選,無視或繞過所有與商業有關的法律,以及鎮壓任何公司內部的工會運動。即使是上市公司,公開的文件也從不說明誰是最重要的決策者(p. 74)。許多外國公司抱怨,名義上是企業對企業的雙邊事務,它們在私人談判中面對的卻是一個國家,而不是一家公司(p. 81)。總而言之,我們認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個「單純」的名詞,已經無法充分反映中國商業運作的實況。
這一點事關重大。例如,WTO義務適用於會員政府,要求各國政府規管其國內的企業活動。但是,如果企業實際上是由政府或黨經營,上述WTO規則就顯然未能產生應有的作用。
以上分析突顯了一個事實:到了二〇二一年,二十七年前制定的現行WTO規則應用在現代國際貿易上,已經有些過時了。而且由於WTO修訂規則必須獲得會員一致支持,受惠於現行規則漏洞的國家不大可能放棄這種好處,因此舊規則無法朝合理的方向修訂。如是之故,現況等同是慫恿各國利用WTO現行規則的漏洞,佔其他國家便宜。基本上,這正是美國對中國的指控。
本質上不公平的經濟競爭
雖然現行WTO規則存在著這些漏洞,但這些漏洞並非帶給所有國家平等的機會,而是系統性地偏袒某些國家。在本書接下來的章節裡,我們將指出,在專制國家企業與民主國家企業的競爭中,後者本質上處於劣勢。
首先我們要強調兩點。第一,雖然我們稍早提到許多WTO規則已經過時,但不公平的競爭並非僅限於適用WTO規則的情況。例如在第六章,我們將說明民主國家的反托拉斯法如何導致不公平的競爭,即便WTO的規則並不涉及反托拉斯。整體而言,專制國家與民主資本主義之間的衝突,也出現在許多與WTO規則無關的領域。
第二,民主國家的企業在與專制國家企業的競爭中處於劣勢時,這種劣勢與競爭效率本身沒有任何關係,而是因為民主國家的法律反映了或明或暗的其他民主價值觀。勞動權利的情況正是如此:在尊重人的尊嚴和實踐勞動權利的國家,企業受各種勞動法規約束,諸如工作時數上限、有薪假期最低標準,以及最低勞動年齡、解僱前必須給予一定通知期的規定。因此,這些國家的企業與那些在勞動權利保障薄弱的國家營運的企業競爭時,必然背負較高的勞動成本。我們當然了解,民主國家之間也可能因為勞動權利保障不同,導致企業營運成本顯著有別,但專制國家與民主國家因為差別極大,競爭不公平的問題不可忽視。
在本書接下來的章節裡,我們將說明相對於專制國家,民主國家這種(因為受束縛導致的)低效率的各個面向。但我們必須強調,我們的討論完全無意推論專制國家(如中國)、半專制國家(如新加坡)或民主國家何者效率較高。正如我們稍早提到的,競爭上的限制源自各國法律上的根本差異,而這種差異反映超越效率考量的道德價值。舉個例子:利用奴隸種植棉花的效率很可能更高,但現在所有民主國家都選擇了廢除奴隸制,並且立法禁止。如果有兩個國家在棉花產業競爭,一個利用奴工而一個不用,我們要明白的是這種競爭根本不公平,而不是急著斷言哪個國家更有效率。
簡而言之,我們認為,專制中國與民主國家的終極經濟衝突,根植於兩者之間的意識形態和價值觀差異。民主國家尊重法治,它們的政府因此根本不可能像中國那樣封鎖網路。民主國家的政府有悠久的相互制衡傳統,行政部門因此根本不可能像中國那樣影響法院判決以偏袒本國企業。民主國家的政府官員根本不能向特定私營企業提供補貼,但中國的官員會公然這麼做。此外,民主國家的所有上市公司都對公眾負責,不像中國的公司只對中國共產黨負責。這些差異實際上是所有不公平競爭背後的關鍵。因為這種差異體現在民主國家與專制政體的根本差別上,我們很難想像應當如何避免隨之而來的經濟衝突。這正是為什麼我們把這些衝突稱為無可避免的「終極」經濟衝突。
政治體制是可塑的嗎?
對「經濟發展促成民主」這假說的另一種批評,涉及現實中的政治運作。我們討論經濟發展如何促成民主時,似乎隱含了一種假設:政治體制是可改變或可塑的,是可能受教育、知識和經濟環境影響的。但是,現實中的情況並非總是如此。專制統治菁英從不願意放棄他們的既得利益;他們總是傾向抵制可能損害他們利益的變革。而且在中國這種列寧主義黨國,「政治體制可塑」的這個假設,顯然是有問題的。在這種列寧主義專制國家,根據其憲法,共產黨/國家是幾乎所有事情的最終決定者。固此,是政治體制決定了市場機制,而不是反過來的因果關係。
誠然,每一種政治制度,無論民主與否,都在某程度上影響或改變經濟的運作,這正是為什麼我們會有反托拉斯法之類的東西。但是,中國的情況在類型和程度上都有所不同。在西方社會,政治系統試圖影響或規管市場時,通常會輕微介入,以促進商業運作和防止市場失靈為目的。相對之下,在中國,政治系統牢牢控制和全面監督經濟的運作,目的是確保經濟運作為黨的利益服務。事實上,當中國宣稱它有一種「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或市場社會主義)時,這意味著中國共產黨已經將西方市場經濟改造成一種截然不同的體制。
例如,在中國,共產黨為了維持它對國家的控制,建立了最嚴厲的網際網路審查機制,被稱為「防火長城」。根據自由之家的資料,在全球瀏覽量最大的一千個網站中,中國封鎖了一百七十一個,此外也封鎖了超過一萬個商業網站。這種封網措施是基於上層的政治決定,而所有經濟活動都必須根據這項上層束縛加以規管和微調。因為這道防火長城,中國人必須使用虛擬私人網路(VPN)「翻牆」,才可以連上外國網站。但這種行為在中國是違法的,而自二〇一七年以來,中國政府對這種活動的監控越來越嚴厲。
如上所述,所有經濟活動都必須根據中國的封網措施作調整。例如,中國民眾若要進入美國電子商務平台亞馬遜的網站是非常不方便的(第三章將詳細討論);因此,如果亞馬遜希望中國民眾能比較方便地進入其購物網站,就必須為潛在的中國顧客建立一個當地版本的網站,雖然這對亞馬遜來說是非常沒有效率的做法。這個亞馬遜中國網站連接一個當地伺服器,而且受中國政府審查。例如,你在亞馬遜美國網站搜尋「天安門廣場」這個關鍵詞,可以找到數以百計的書籍和相關商品。但如果你在亞馬遜中國網站上做同樣的搜尋,只能找到不到五項商品──所有其他項目都因為中國的審查而被刪掉了。由此可見,亞馬遜的全球業務必須因應中國的政治運作加以調整;政治是不可塑的,商業活動才是可塑的。
另一個例子是:在中國,任何組織裡有超過三名共產黨員,就必須建立黨組織,而所有上市公司都有一名黨委書記坐鎮公司董事會。因為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統治政黨,公司所有的政策都必須接受黨的監督。此外,由於中國共產黨的運作不透明,這種內部控制機制當然會妨礙公司對其股東和債權人負責。這再次說明:在中國,是政治體制改變了經濟規則和活動,而不是經濟活動影響政治體制。
上述例子告訴我們,在專制政體中,尤其是在列寧式共產主義國家,被改變的是經濟活動,而不是政治體制。因此,在這個全球化時代,民主國家的企業面臨來自兩個不同源頭的經濟競爭:有些競爭對手來自體制相似的民主國家,有些來自政治意識形態完全不同的專制國家。如此一來,我們自然會問:這種競爭公平嗎?在這種競爭中,哪一方本質上佔有優勢?後面的章節將分析這些問題。
二十一世紀專制統治者的不義優勢
影響經濟和政治交互影響的另一個因素,涉及近年的科技發展。艾塞默魯與羅賓森(Acemoglu and Robinson, 2012, 2019)和拉詹(Rajan, 2019)皆強調可以制衡國家權力的「社會」或「社群」力量。艾塞默魯與羅賓森提出了他們的窄廊論:民主和經濟成長能夠穩定發展和維持的參數範圍,只存在於一個非常狹窄的窄廊地帶之中。在我們看來,最近的科技發展很可能將使這道窄廊變得更窄,專制國家變得更容易維持其運作的穩定性。
我們知道,從專制統治轉向民主必然涉及某種「社會運動」──或是一場殘酷的革命,或是一連串的和平抗議,例如二〇一〇至一二年阿拉伯之春期間的著名集會。阿拉伯之春之後,許多社運人士開始意識到,社群媒體是動員社會集會和抗議的有效工具。但另一方面,國家權力機關也意識到,網路上的溝通交流能夠推動反政府運動。這促使國家對網際網路實施更有效的控制。因此,雙方都試圖充分利用網際網路:一方希望利用網路動員社會力量,另一方希望利用網路遏制社會力量。問題是:哪一方可以佔據優勢?
我們認為,在網路時代,國家權力機關佔有優勢。促使我們得出這個結論的,是大數據和人工智慧這些關鍵科技發展。大數據方面,政府自然掌握了來自人口紀錄、戶籍、租稅申報、房產登記、交通監控、銀行信用紀錄、公共交通監視器、公有電信足跡、全球衞星定位系統(GPS)等資料。相對之下,社會團體或組織很難取得這些資料。如果政府想利用這些大數據監控公民社會的反對力量,它有可能掌握境內(和甚至境外)每個人的一舉一動。
如果上述大數據掌握在專制國家手上,政府運用這些資料時還有一個優勢:利用人工智慧技術。需要注意的是,大數據的運用通常涉及複雜的平行計算演算法和極快的運算速度。這種設備對社會團體來說非常昂貴,但專制國家可以輕易取得。因此,大數據配合人工智慧技術,不成比例地增強了政府的能耐,更能夠監控社會團體、了解其網絡、先發制人阻止其集會,或甚至分化這些團體。
最著名的例子當然是中國,它公開吹噓其社會信用系統,該系統記錄每一個人過去的行為和言論,並為每一個人「打分數」。這種分數被用來決定當事人是否可以購買高鐵票、他們的孩子是否可以入讀優質公立學校、他們能否得到申請的工作,以及他們會不會被起訴犯了某些罪。隨著政府利用大數據和複雜的人工智慧演算法監控民眾,可以預料,社會制衡力量將嚴重受限,專制國家將更難轉向民主。
在民主國家,大數據和人工智慧則不會那麼令人擔憂。民主國家最大量的數據資料可能來自臉書、Google和亞馬遜,每一家都只能獲取用戶的一部分私人資料。民主國家也有比較全面的隱私保護法,它們的憲法也不可能容許合併使用這些不同企業擁有的雲端資料。
總而言之,我們認為在這個大數據和人工智慧數位時代,專制國家在壓制社會力量方面佔有顯著優勢,它們因此比以前來得穩定。因此,我們預期民主國家與專制國家的對抗將是曠日持久的。如果這兩個陣營的企業之間有一些根本不公平的競爭情況,我們預期這種情況將持續頗長時間。本書的目的,是辨明這種不公平競爭的各個面向。
有可能溫和競爭嗎?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的不公平競爭面向,有些已經出現在美中衝突中,例如不公平的政府補貼和市場准入(第二章和第三章);但也有一些面向還沒有,例如反壟斷制約(第六章)。即使是那些已受矚目的面向,外界也只是指出了不公平競爭的事實,但未能闡明這種衝突的理論結構。在這本書中,我們試著系統性地分析所有這些不公平競爭面向。我們清楚地指出民主國家為何對企業經營環境施加一些當然的限制,以及專制國家為什麼沒有這種限制。因為這些限制內建於民主制度裡,導致民主國家與專制國家之間的不公平競爭無可避免,而專制國家總是會利用這種情況取得優勢。
在前面的討論中,我們提到,民主制度內必然有許多相互制衡;民主國家的經濟活動受人權和個人自由之類的價值制約,而這通常會降低效率。專制國家不受那些價值制約,因此可能更有效率。撇開內在民主價值可能降低效率的問題,民主國家是否在某些方面佔有優勢呢?艾塞默魯與羅賓森認為答案是肯定的(Acemoglu and Robinson, 2012)。雖然這不是本書的重點,但我們認為值得在開頭非常扼要地說明一下。
艾塞默魯與羅賓森將經濟制度分為廣納型(inclusive)和榨取型(extractive)兩大類(Acemoglu and Robinson, 2012)。在廣納型制度中,產權明確,多數人可以分享經濟成長的成果,而且憲法的訂定就是為了確保這種利益共享的規則。相對之下,在榨取型制度中,少數統治精英拿走了大部分經濟成長成果,產權未能得到有效保護,而且制度的設計就是為了配合這種榨取。因為這種榨取型制度設計,人們參與經濟活動的動機不強,在精英專制控制下的經濟表現因此會比較差。廣納型制度的典型例子是穩定的西方民主國家,榨取型國家的典型例子是菲律賓、印尼和一九六〇年代的一些拉丁美洲國家,它們實行由少數統治菁英主導的權貴資本主義。
艾塞默魯與羅賓森指出,雖然中國過去三十年間經濟成長速度很快,但這應該是因為中國處於經濟發展的早期階段(Acemoglu and Robinson 2012, Chapters 3 & 15)。艾斯等人的說法是:中國之前經濟成長快速,是因為該國處於要素驅動和效率驅動的經濟發展階段(Acs et al., 2000)。這些階段的經濟成長類似從生產可能性邊界(production possibility frontier, PPF)內部向PPF曲線移動,成長源於「移除原本不效率的因素」,成長速度有可能非常快。而一旦經濟已經接近或處於PPF曲線上,進一步的成長就必須靠創新驅動。艾塞默魯與羅賓森聲稱,中國經濟進入這種創新驅動階段之後,該國的榨取型制度將導致經濟放緩。
倘若一如艾塞默魯與羅賓森所稱,在創新驅動成長的時代,民主的廣納型制度優於專制的榨取型制度,這是否意味著我們不必擔心現階段的競爭不公平問題呢?我們是否可以忽略這些問題,並期待民主與專制體制之間終將有平穩的競爭呢?我們認為答案是否定的,論據有以下四點。
首先,當我們說系統A比系統B更有效率時,我們沒有考慮A與B之間的交互作用。但是,兩個系統真的在全球化貿易體系中互動時,情況就會變得比較複雜。例如,在具有報酬遞增或網絡經濟特質的高科技產業,現在的領先者很可能在未來保持領先或甚至擴大其優勢。正如我們將在第二章指出,這種報酬遞增特質使政府有額外的誘因去補貼本國高科技產業,以便在未來佔得優勢。因此,如果美國的高通公司因為中國巨大的政府補貼而在5G或6G競爭中輸給了華為,在報酬遞增的情況下,高通要在未來幾代的電訊競爭中扭轉敗局是極其困難的。這意味著今天產生的不公平可能長期存在。廣納型制度的上述創新優勢,可能完全沒有機會發揮其作用。
第二,有些受高度管制的產業是有「標準」的,而誰的產品最先上市,誰就可能成為市場標準。這一點也會吸引專制國家的政府提供補貼,而在標準確立之後,民主國家的公司就可能被迫終止營運,雖然它們的產品可能更好。
第三,當我們說系統A比系統B更有效率時,這是一種假設所有其他條件相同之下而做的比較。但政府的支持是一種額外的力量,擾亂了不同國家企業之間的競爭,「所有其他條件相同」的假設因此不再成立。如果我們容許所有政府補貼本國企業與外國企業競爭,那麼競爭就是在政府之間,而不是在企業之間,而整個國際貿易的背景也會改變。
第四,有些商品或服務可能直接關係到國家安全。例如,6G對精準的地理定位極為重要,而這對衛星、GPS和高科技戰爭至為關鍵。TikTok或任何應用程式若使用人工智慧作為其演算法設計工具,可能會蒐集極其有用的個人資料,以便在未來能夠精確地傳播資訊。兩者顯然都很可能出現危及國家安全的情況。如果涉及國家安全相關技術的公司是臉書或Google之類的私營企業,民主國家可能不會那麼擔心。但如果有中國共產黨控制的公司參與其中,則許多國家將會極其擔憂。因此,在攸關國家安全的行業,民主國家與專制國家之間的競爭是無可避免的。這是不大可能出現溫和競爭的一個領域。
我們為何聚焦於經濟衝突?
我們之前提到,中國與美國和其他民主國家的衝突,根植於民主與專制主義的根本價值差異。我們也指出,在許多國家,這些價值超越純粹的經濟效率考量。例如,中國嚴格管制網際網路的使用,這顯然違反表達自由、資訊自由流通、新聞自由之類的民主價值。那麼,為什麼我們會想研究這種對自由的壓迫造成的經濟影響,而不是自由本身呢?
事實上,我們的分析方式的確是顧及了國際政治的實際運作。在現實國際政治中,每當專制國家被指控侵犯人權(例如迫害某個群體或禁止某些活動),它們通常會這麼為自己辯護:「這是我國的內政問題。這些人和他們的活動使我們擔心國家安全受損,我們已經按照本國的法律處理問題。」以網際網路的監理為例,世界上每一個國家都會限制色情內容或影片的傳播,但各國的限制可能各有不同,有時也可能因地方宗教團體而異。因此,我們很難在控訴一個國家侵犯人權,與干涉該國內政之間,劃出清楚的界線。
但是,經濟衝突使我們能從另一個角度切入問題。在國際競爭十分普遍的全球化時代,競爭環境理應公平是世界上幾乎每一個國家都能接受的概念。雖然A國可能沒有正當的理由去過問B國的網路管制程度,但如果B國的網路管制政策系統性地造成市場准入問題,導致A國的電子商務平台面臨不公平的競爭環境,那麼A國就確實大有理由去挑戰這種不公平的貿易行為。因此,概念上而言,批評不合理的政策本身有時只是徒勞,但批評這種政策所造成的經濟影響卻很有作用。出於策略考量,本書的焦點確實是民主國家與專制國家的價值觀差異在經濟層面產生的影響。我們認為這種策略或許比較能夠避免被批評的國家搬出「這是內政問題」的藉口。
自一九九四年《馬拉喀什協定》頒布以來,世界已經有了一套關於貿易和經濟活動的共同規則。《關稅暨貿易總協定》、《服務貿易總協定》、《與貿易有關之智慧財產權協定》和《補貼及平衡措施協定》之類的協定,已經成為公認的準則,獲世上多數國家接受為經濟互動的基礎和規則。截至二〇二〇年底,採用上述貿易規則的世貿組織共有一百六十四個成員。此外,WTO還有一個爭端解決制度,可以在成員投訴其他成員違反貿易規則時作出有約束力的裁決。簡而言之,不同於各國可能有巨大分歧的自由或人權問題,許多經濟衝突在現行WTO制度下可以相對容易地做出裁決。
就私人企業而言,公平的商業競爭規則和公平的競爭環境也是個別企業的訴求。商界人士可能不大了解A國的封網措施如何侵犯人權,但如果這種措施導致A國民眾無法進入B國的電子商務平台,那麼這種不公平的經濟影響就很容易察覺。因此,如果我們聚焦於侵犯人權的經濟後果,我們往往可以比聚焦於人權問題本身得到更多關注和支持。如果我們得到的支持和關注足夠強大,我們就有可能藉由從經濟衝突切入,間接導正人權問題。
當然,並非所有的意識形態分歧都有經濟後果,我們從經濟衝突切入的做法因此有其侷限。事實上,我們並不認為我們能夠解決很大範圍的問題。我們的努力也許無法創造一個理想世界,但我們確實希望我們能夠幫助世界變得好一些。
本書的結構
本書其他章節的組織結構如下。第二章先分析二〇一八年引起美國、歐盟和日本強烈反應的「中國製造二〇二五」計畫。我們解釋了該計畫背後的主要爭議,以及民主國家不高興的原因。第三章審視專制國家控制網際網路造成的經濟後果,並解釋為什麼這為電子商務製造出不公平的新貿易壁壘。在第四章,我們討論網路時代不公平競爭的另一個面向:隱私與國家安全。這與最近人工智慧的發展有關。因為保護隱私是民主社會的一項基本價值,我們認為很難有妥協折衷的解決方案。
第五章討論上市公司的問責問題,並解釋中國與民主國家相關法律的根本差異。這些法律在這兩種體制之間製造出不公平的競爭環境。第六章涉及反托拉斯法,這是討論國際經濟衝突的文獻以前不曾觸及的一個領域。民主國家制定反托拉斯法,基本理念是希望建立一種制衡制度,而這在專制國家卻是個荒謬的概念。我們將說明這個概念差異如何衍生不公平的競爭。第七章討論國家安全問題。由於中國共產黨可以由上而下將各種國家目標強加於企業,這導致民主國家的國家安全體系必須開始審查來自中國的外商直接投資(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近年來,這些原本是遇到特殊情況的例外審查,漸漸變成是優先的審查事務。這當然會使民主國家的經濟活動變得比較沒效率。第八章討論司法救濟。在民主國家,司法系統是獨立的,所有國際企業如果在其他國家的競爭中面臨不公平的待遇,都可以尋求可靠的司法救濟。但在中國這種專制國家,根本沒有司法獨立這回事。因此,外國企業試圖在專制國家尋求司法救濟時,往往面臨不公平的待遇。最後,第九章彙整我們的發現,並提出一些結論。
上述的民主與專制國家的體制差異,往往體現在各種法律上。因此,我們分析國家之間的衝突時,往往得出這種推論:「如果民主或專制國家的法律往特定方向修訂,就可以避免衝突。」但是,我們也往往發現,以那種方式修訂法律會違反民主的基本價值,或違反專制國家的基本定義。這正是為什麼我們認為,那種衝突最終是無可避免的。因為我們在確立論證的過程中分析了各種法律,因此這本書也可視為一本分析法律和法制的書,分析的對象是現行WTO的規則。
總之,這本書並不是要幫助讀者認識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運作;我們主要是關注中國與民主國家市場經濟體的互動。我們也不把美中衝突歸咎於任何一個人(例如習近平或川普),而是致力指出中國體制與西方民主國家不一致之處。根本而言,真正重要的是體制,而不是制定和濫用體制的個人。我們認為,美中之間的貿易戰和其他經濟衝突只是表面現象,其下有深刻的體制差異,簡而言之,是民主與專制之間的差異。
有些人傾向將美中衝突稱為「修昔底德陷阱」,認為崛起的強國遇上現存霸主,難免陷入對抗。但我們不會以這種簡化方式看待美中衝突。如果單純只是兩個實體之間出現修昔底德陷阱,那就只是權力鬥爭,並不涉及價值觀。但是,在民主與專制之間,價值觀的差異至為關鍵。美國與中國的對抗,不像修昔底德陷阱那樣迫使雙方陷入其中,而是體現了雙方的價值差異,如此的差異迫使雙方相互對峙。我們的結論是:終極經濟衝突必將發生在意識形態截然不同的兩個陣營之間。
中文版序與導讀
序言
推薦序_孔傑榮(美國外交關係協會亞洲兼任高級研究員)
縮寫列表
第一章_引言:當「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走向世界
第二章_中國製造二〇二五:政府補貼的問題
第三章_電子商務重商主義:封鎖網路的問題
第四章_禁止TikTok和微信:隱私保護與國家安全問題
第五章_制定《外國公司問責法》:上市公司問責問題
第六章_全球化時代的反托拉斯法:競爭中立問題
第七章_跨國併購管制:國家資本主義問題
第八章_強制技術移轉:補救不足的問題
第九章_如何與龍共舞?
註釋
參考書目
書籍代號:0LYO0048
商品條碼EAN:9786267052853
ISBN:9786267052853
印刷:單色
頁數:352
裝訂:平裝